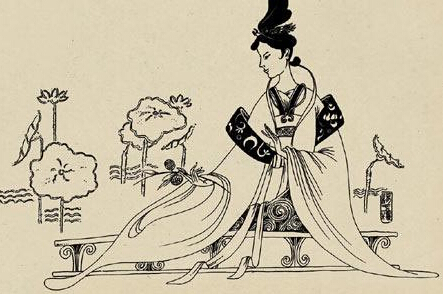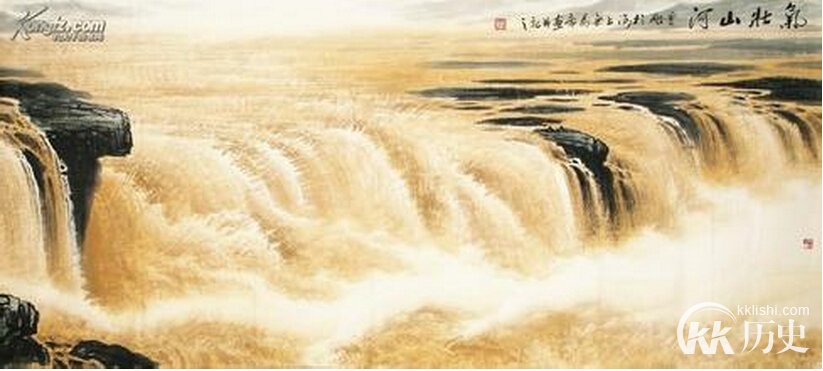皇上,我不会画“春宫图”!身边这男人是块石头,连情爱都不懂!野史趣闻
文 |仙子有病
微信公众号 | 红颜手札
“红颜手札”每天为您推送文章
“什么风流子,叫作下流子还差不多……”
月上柳梢头,大延第一花楼蝉春楼渐渐热闹起来,谈笑声伴着丝竹管弦一声高过一声。韩香打着哈欠自厢房里走出,途经一间最富丽堂皇的厢房时,冷不防听房中传来这样一句话。
恰巧,这人口中所说的风流子不是别人,正是她韩香。
全大延最有名的春宫画师风流子无端听了这样一句话,思索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没忍住,抬脚便跨了进去。

房里坐着位玄衫公子,身边伴着蝉春楼行情最好的花娘。见有人进来时抬起的一张脸长得倒是人模人样,怎么说起话来这么不中听呢?
韩香一拱手,道:“扰了公子雅兴实在抱歉……只是方才听公子在评论风流子,想来讨教公子高见。”
玄衫公子眯起眼,饶有兴味地打量她片刻,悠悠笑起来:“阁下是?”
“在下便是风流子。”
玄衫公子轻笑起来,韩香顿时忍不住了,脸上也带了些愠色:“莫非公子也像那些凡夫俗子一般,认为这春宫图是上不得台面的淫秽之物?”
“倒也不是。”那人轻摇纸扇,目光在桌上的春宫图上一扫:“一幅上好的春宫图应当艳而不俗,情而不淫,看你谈吐也不像是市井出身,落笔怎么这般俗不可耐,当真以为画些妖精打架就能称春宫了?”
韩香顿时红了脸,恼羞成怒道:“你怎知我画不出那样的春宫!”
那玄衫公子一笑:“不然,来打个赌如何?十日之后,还在这蝉春楼,你若画得出我所说的春宫,我便称你一声师父,若不然,那你风流子就得绕着这蝉春楼狗爬一圈,如何?”
“赌便赌!你这一声师父,为师就先收下了!”
定了赌约,韩香走出那厢房,怒气尚未完全平息,冷不防地身后冷冽的男声响起:“先前我还以为只是声音相似,没想到还真是你……”
熟悉的声音让韩香如遭雷击,站在那里头也不敢回。
“转过来!”
韩香唯唯诺诺地转过身来。男子不知道在门外听见了多少,只是紧紧拧着眉头,一双狭长凤眸冷冰冰地望着她。韩香低下头,讷讷地唤了声“师父”便不再说话了。
“风流子?我倒不知道我竟教出这样一个好徒儿!”
“师父……”
夜深人静。世人所道的风流佳公子,全大延的大姑娘小媳妇提起就脸红心跳的春宫画师风流子阁下正待在薄府书房——跪书案。
自小就跪惯的书案还是一贯的冷硬,可就算如此,也抵不住一阵阵睡意的来袭。韩香直着身子,脑袋却一点一点往下垂。
书房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韩香顿时睡意全无,战战兢兢抬起头来。薄元青余怒未消,依然冷着一张脸:“知错了?”
“知错了!”
“错在哪儿了?”
韩香垂下头,不说话了。
“你真是让为师长见识了,春宫好手风流子?若不是今日陪几位大人去那儿恰巧碰见,你还打算在那乌烟瘴气的地方画多久这种……”他顿了一顿,恨声道,“这种淫秽之物!”
一天内被打击两次,韩香倔性子便也上来了,直起了身子道:“师父错了,弟子画的不是淫秽之物。”
“哦?”薄元青怒极反笑。
韩香坦然地对上他的眼睛,道:“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和喝水吃饭一样。既然做得,为什么画不得?看不得?说不得?”
薄元青被她这样坦然的态度一惊,一时间竟然说不出反驳的话来。
说起来,似乎从未曾见过自家师父同什么姑娘亲近过,早过了弱冠之年,却连妻妾也不曾有一门。想到这儿,她不禁更加纳闷了:“师父,你有喜欢的姑娘吗?”
“你……放肆!”
知道自家师父是个色厉内荏的角色,韩香其实并不怕他,自桌上挪了挪凑近来,仰头望着他:“师父,你该不会,还不曾爱慕过一个姑娘吧?”
那吞梅嚼雪而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红了耳根,韩香看在眼里,当真为自家师父的纯洁傻眼了。
不去看自己这恼人的小弟子,薄元青愤愤地甩袖走了。
师父走后,韩香从书案上下来,想起那玄衣公子的话,她自床下翻出自己以往所画的春宫图册,仔细打量起来。
“当真有这么低俗不堪?”
十三岁起便扮作男儿,韩香作为一个女子的羞耻心实在淡薄得很。
熄了灯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睡去,明明是已经疲惫至极,韩香却仍是做了一晚的绮丽春梦。梦中那人一双狭长凤眸冷淡至极,却也无端撩人至极。
清晨醒来,望着镜中人的满面潮红,即使韩香自认“见多识广”,也不由得暗暗心惊:她不会是,对着不该的人起了不该的念头吧?
起床后,洗漱完毕,也收拾好了情绪,薄元青便遣了小厮来,说让她收拾收拾随他一起入宫。
拜在师父门下已有六年,这却是韩香第一次随着师父进宫面圣。韩香大概能猜出,这次是为选秀画像的事情。
到了殿中,韩香跟着薄元青站在一众画师中,抬头望了一眼,当即便傻在原地——那人不就是与她打赌的玄衣公子么?
韩香垂着头,极力将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却没想到最终还是被认了出来,年轻的皇帝一脸促狭笑意,悠悠道:“听闻薄太傅的小弟子擅画人物,所绘的……极其传神啊?”
其中略掉的字词让韩香暗暗心惊,皇帝却话锋一转,道:“既然如此,此次选秀画像的事情,便由薄太傅负责吧。”
师父擅画山水,从不画仕女像,韩香悲伤地想,这回惨了……
自宫中出来后,一众画师便打着风流名义去蝉春楼喝花酒,纵使薄元青是浊世清流,无奈因着此次主事人的身份不得不前去作陪。
坐在马车里,看着面前的薄元青冷着脸一语不发,韩香更不安了,只好把那赌约的前因后果和他说了。
乖乖地挨了理所当然的一顿数落,韩香理亏,低头不语,于是自家师父那一脸的恨铁不成钢便更明显了。
“平时练习不见你这样认真,闯祸倒是个好手。”
见他语气和缓下来,韩香连忙凑过去,笑嘻嘻地道:“徒弟闯祸师父收拾,天经地义!”
话一说完,想象中的训斥却没如期而至,韩香抬头,望见那人蕴着复杂情绪的眸子,当下一愣。
“罢了……”最终,那人如是道。
韩香在蝉春楼是熟客,但碍于自己才在这儿闯下大祸,全程她都低着头作忏悔状,企图以此争取宽大处理。
一群画师看不上她这样的小角色,劝酒自然全都朝着薄元青去了,他少有应酬,几杯下去,白皙瘦削的面颊便染上了几分潮红。既然全是男子的筵席,便少不了花娘作陪,席间也有人讲些荤腥段子,薄元青转头望她一眼,不禁皱眉。

众人酒意正酣,搂着花娘的动作也渐渐开始不规矩起来。薄元青放下酒杯,自桌下拉住了她的手。
带着些微凉意的修长手指扣住了她的手腕,明明不是什么暧昧姿势,韩香的心却是一悸。
还没反应过来他已拉着她起身辞别,韩香一脸茫然。上了马车才听他恨恨道:“你一个女儿家,不知羞……”
韩香愣了愣,才明白过来他说的是方才筵席上那荤段子的事。其实听那一两个荤段子于她而言并没什么,若要认真计较起来,她还能讲两个更荤的,但想想自家师父肯定不喜欢听到这样的答案,于是韩香只好低头装娇羞。
翻来覆去一夜也没能好好入睡,第二天韩香无精打采地坐在桌前面对着摊开的画纸发呆。
如何画一张艳而不俗情而不淫的春宫?
依旧是毫无头绪。
直到薄元青来时,她仍一笔未下。他皱眉望着她桌上摊开的画纸,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又极不自然地转开眼去,道:“你与皇上的那个赌约……”
“想不出来……”韩香撑着头,两眼呆滞。
薄元青依旧皱着眉,自他进来后,皱起的眉头就没平下去过:“你以往的那些‘画作’呢?拿出来我看看。”
韩香顿时苦下脸:“不要了吧?师父。”
就看见她听个荤腥段子都能指责她身为女儿家不知羞,要是让他看见她画的春宫,岂不是要被骂大逆不道?
“拿出来。”
韩香看了看自己师父固执的神色,无奈地自床底拖出一口箱子。她所有春宫集子的原稿都在此了,想了想,她又在箱中挑挑拣拣,努力翻出几本……嗯,衣裳比较多的,然后递了过去。
虽说已经知道自家徒弟私下里在干些什么勾当,但知道和亲眼看到之间,总是隔着巨大的鸿沟。薄元青捏着手上薄薄的册子,每翻一页,神色就更冷一分,韩香咽了口唾沫,十分不安。
薄薄一本册子那人足足翻了一盏茶的时间,面色也从红至黑,最后,他将册子一摔,恨声道:“韩香,为师当真是小瞧你了。”
随即拂袖而去。
韩香捡起地上的小册子,正嘀嘀咕咕着“都说了别看嘛,看了又要骂师父的心思好难猜……”
没料到那人居然又折了回来,手朝她一摊:“拿出来。”
“什么?”纳闷地望了望他,韩香试探地将那册子重新递给他。
那人强自镇定地翻开图册,冷然道:“画得一塌糊涂!”
修长手指在上面点出几处:“此处的线条虚实不分,为师是怎么教你的?还有这儿,墨色虽深却未罩匀,少了透明之感……”
虽说是自己所画的春宫,可被人这样指点,韩香面颊也是滚烫如火。抬头望去,那人面颊至耳根都泛着淡淡桃色,却依然是一副冷眉冷眼的面孔,见她望过来,不自在地瞪她:“作甚?”
“师父你脸好红啊。”
“闭嘴!”
薄元青走后,韩香坐在书案后继续思索那幅打赌的春宫,视线自桌上滑过,落到方才被指点的那本春宫集子上,韩香沉了沉思绪,忽然眼睛一亮,提笔便开始画。
十日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约定的日子到了,韩香悠然换了风流子的衣衫,前去赴约。
日暮西垂,蝉春楼比起往日还要热闹几分,大延第一春宫好手的赌约无疑已经传了出去,有好事之徒早早便守在那里,等着看一幅好春宫图,或者是一场好戏。
韩香到蝉春楼时,那人早就到了,依旧是一身玄色衣衫。韩香知趣地没有揭穿,只是不敢再像上次一般傲气,只规矩地将所带的画册置于桌上。
皇帝带笑的眼扫过她,拿起桌上的图册翻开。只看一眼,便愣了愣。
画中两人衣衫皆整整齐齐一丝不苟——这算哪门子春宫?
依次翻过去,画中男女都是那两人,所描绘的也都是些生活场景。诸如宴席上男子自桌下扣住女子的手腕,拉她离席;书房中,男子站在女子身后,教她执笔;花园中,男子低头,替女子解下不慎钩住头发的花枝……
整本图册看下来,画面清雅,色彩明丽,一丝淫意也无,其中所透出的缠绵悱恻意味却是令人会心。
皇帝合上图册,抬眼看了韩香一眼,见她一脸坦然,丝毫扭捏也无,也是一笑,意有所指道:“当真是……名师出高徒。”
话音刚落,杯盏碎裂的声音自身后响起,韩香回头,薄元青不知何时起已站在她身后了,方才那本春宫集,想必也看得一清二楚了。
见她回头望过来,他丢下手中捏碎的杯盏,冷淡地扫了她一眼,转身便走。
再顾不上输赢,韩香抬脚追了上去。

那人是真恼了,越走越快根本没有等她的意思。韩香追不上,情急之下连忙装作崴了脚,一声痛呼后,前方身影果然停了下来,转身慌忙走过来,低下来查看她的脚踝。
“师父,我……我喜欢你。”韩香抬头望着他,道。
那人一怔,面色一寒,站起来恨恨地看着她。
“你当真是长本事了……连师父也敢作弄?”
既然都说了出来,韩香也顾不上害羞了,拦在他身前,抬头坦然对上他的眼睛:“师父,我喜欢你。真心的,不是作弄!”
薄元青怔了怔,霎时从脸颊红到了耳根,半天才不利索地训斥道:“胡闹!”
韩香低头想了想,鼓起勇气抬手拥住那人,睁着眼睛便吻了过去,薄元青猝不及防,被吻了个结结实实。
柔软,滚烫。
韩香睁着眼,他也睁着眼望她,半晌,他才仿佛大梦初醒般一把将她推开。
“师父,我喜欢你,真的。”这个晚上,韩香已经是第三次说这样的话了。
那人却仍是一副镇定面容,皱眉道:“你一个姑娘家,知不知羞!”
“我喜欢师父,不知羞!”
韩香不是不知羞,只是她既然连春宫都能画了,自然也早将男女之事看得通透明白了。喜欢一个人,为之脸红心跳不能自已,本是天理,大方磊落,有什么可羞的?
她先前不明白自己喜欢薄元青,如今想明白了,就更加“不知羞”了。一心只想求一个肯定的答复。
他外出时,她跟着,锲而不舍地问:“师父,你喜不喜欢我?”
他在房中作画时,她守着:“师父,你一定是喜欢我的对不?”
他吃饭时,她看着:“师父,你肯定喜欢我!”
薄元青不堪其扰,可又丝毫办法也无,冷脸也做了,训斥也训了,对韩香而言,这些都无关痛痒。
这日傍晚时宫里来了消息传他进宫,韩香不能随着,只好去书房打发时间。
手中的墨笔在画纸上漫不经心地勾勒,她其实早不知走神到了哪里。
初拜入他门下时,韩香其实并不大喜欢那人,他太过沉闷,作为老师又着实严厉,每次都只是让她习画。有次她玩闹的时候不慎毁了他一幅费时半年的山水,本以为死定了,那人却只是拧着眉头训斥了她一顿便作罢,也就是那时候,她就知道自家师父只是个纸老虎,后来就不再怕他了。
回过神来时,才猛然发觉自己已在纸上勾勒起了那人的轮廓眉目。她放下笔,撑着头靠在桌上昏昏欲睡,猛然惊醒时,书房的门恰恰被夜风带上。颊边似乎还残存着一点点温暖湿润的触感,她怔怔地抬手去触了一下,霎时明白过来,咧开一个明朗的笑。
她匆匆跑去拉开门,果不其然,夜色中那个身影还未走远。她在书房门口跳起来,笑道:“师父你喜欢我对不对?我就知道!”
望见那修长挺拔的身影微微趔趄了一下,然后继续仿若未闻般地往前走,韩香笑得更是春风得意。
秀选结束后,韩香也开始忙碌起来,师父擅画山水,却不擅长画肖像,于是进宫给秀女画像的任务便留给了韩香。
韩香画得一手好春宫,仕女图自然也不在话下,而刚刚入宫的秀女对她这画师也相当配合,唯一令韩香比较烦躁的便是皇帝总是出现在园中,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打量着她。那人身在高位,眼光自然比常人毒辣,估计一早便看穿她是女儿身,而一个男子这样肆无忌惮地打量一个姑娘是何意,韩香又不傻,自然是知道的,但无奈那人得罪不得,韩香只好装傻。
好不容易捱到日暮西垂时,才算得以解脱。用了晚膳后,韩香又跑到了薄元青的书房。
那人近来在躲她,明明躲得十分刻意,偏偏又要装作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韩香刚刚进门,他便收了笔要出门去。
“师父,”韩香慢悠悠地叫道。
那人驻足,头也不回,问:“作甚?”
韩香将几张画铺到书案上,神色颇为认真:“弟子今日进宫为秀女画像,自己觉得不甚满意,还望师父指点一二。”
薄元青皱了皱眉,还是走了过来:“何处?”
韩香在纸上随意点了几处,那人皱着眉,十分认真地低头打量道:“构图尚可,只是用色过于艳丽了些,还有……”
未待他将话说完韩香便嬉笑着仰头亲上了他的唇角,然后便发现那人明显一愣,僵直了身体。
薄元青反应过来后,一把推开了她,厉色道:“你这是作甚?”
“师父不知道吗?”韩香凑上去,笑嘻嘻地望着他,问:“那师父那晚偷亲我又是为何?”
薄元青拉开了两人距离,严厉道:“不许胡来!”
被他这么一吼,本来不想胡来的韩香也想胡来了,再次欺身而上,笑道:“我偏要胡来!”
薄元青身后便是书案,无处闪躲,身前那人又是行为放荡,就连手也不规矩,他便一把捉住她手腕捏在她身后,却没想到两人顿时贴得更近了。柔软躯体贴近的感觉让他顿觉喉头干涩,躲闪不及被那人吻了个正着。
他霎时有些失神,随即听到那人低低的一声笑,待抬眼看去,正对上那双带着笑意的莹亮的眸,薄元青瞬间清醒过来,一把便推开了她。
“不知廉耻!”
三番五次被推开,再听到这句话,韩香顿时仿佛被当头泼了一盆冰水,薄元青一腔热血霎时冷却下来。
薄元青看她一脸错愕,微微启唇似乎是想说什么,最终却仍是冷淡地抿了抿唇,抬手理好凌乱的衣襟,转身走掉了。
韩香站在书房里,忽然觉得有些难堪。

她一直觉得那人肯定是喜欢她的,但是如今看来,或许是她错了,她原以为那人是一块冰,总有捂化的时候,但没想到,那人却是一块冷硬的石头。
石头哪里会懂什么情爱呢?
韩香情绪很是低落,作画时状况频出,于是称病,要请几日假回家。她所谓的回家不是回薄元青府上,而是回自己家。
想起那夜自己还有几张秀女画像落在他书房中,韩香也只遣了下人去拿回,他要躲她,她也不想再一厢情愿地凑上去,惹两人都不痛快。
韩香连包袱也未曾收,只身一人便回了韩家。
在家中待了小半月,那人也一直不曾来过,连一声问候都不曾有。大延来了消息时,韩香还待在家描丹青,一幅一幅都是那人面容。
来人不是薄元青,是宫中的公公。
那人在庭中冠冕堂皇地念完圣旨,笑吟吟地抬头望她:“韩姑娘好福气,诸多秀女画像中,圣上一眼便钦点了姑娘呢……”
韩香微怔,画像?什么画像?
跟着公公在驿馆看见那幅画像时,韩香更是愣住了。
那幅画纸张微微泛黄,但画上的姑娘确实是她没错,准确地说,是她拜入薄元青门下没几年的时候的样子,那时她刚刚及笄。画上姑娘一身白衣,仅用一根玉簪将乌发束起,侧脸娇俏天真。坐在竹林中垂首描一幅丹青。
她上前去,细细看那幅画,虽不是她所画,但那画风却与她所差无几。她转身问一旁的宫人:“这画可都是自薄太傅府上拿来的?”
那人一愣,点了点头。
韩香抿起唇角,笑意几乎再也藏不住。还未等那宫人反应过来,她转身便出了驿馆门,跨上马,朝着大延方向绝尘而去。
半月未见,薄府依旧,门口的守卫见策马而来的姑娘下了马便要往里冲,当即便要拦,可伸出去的手却在空中滞住了,怔怔道:“小韩公子?”
韩香脚步未停,边走边问:“师父呢?”
“大人?大人进宫面圣去了,小韩公子,你……”
韩香摆摆手,径自朝着书房的位置走去。
自桌上翻了一圈没寻到,她敲敲额角,在屋中思索了一番。挨个儿掀开书房中的山水图,终于在最后一张画后寻到了其中乾坤。
推开暗门,韩香抬眼望去,斗室中挂着无数幅仕女图,其中女子或坐或站,或凝眸或展颜,神态不一,可确确实实都是同一个人。
阳光照进这画室,画中女子笑如春山,栩栩如生。
她弯起唇角,十分肯定道:“我就知道,你肯定喜欢我!”
大殿中此时的气氛却是十分阴冷,皇帝失手打破了一个杯子,满堂惊寂,他漫不经心地召人收拾地上的碎片后,道:“抱歉,方才太傅的话朕没听清,太傅再说一遍吧。”
薄元青依旧是一贯的沉静面容:“臣请皇上为臣赐婚。”
“哦?敢问是哪家女子如此好福气,竟能让太傅青眼有加呢?”
薄元青垂首:“城外韩家,韩香。”
“荒谬!这韩香分明是你门下弟子,况且还在本次秀选名册之内……”
“实情究竟如何,陛下明白。”他仍是不卑不亢。
皇帝打量他半晌,却是低笑起来:“太傅身为人师,却与自己弟子纠缠不清,实在有违师德吧?”
殿中气氛一时凝结到冰点。
还未等他回答,便有人匆匆赶到,十分坦然地将衣服下摆一掀跪下了:“民女韩香参见圣上。”
薄元青转头一望,心里顿时便是一惊,皱眉低声问她:“你来作甚?”
韩香却是没理他,径自对着皇帝道:“民女和圣上曾有一赌约,不知圣上还记不记得,若圣上记得,民女想知道,这赌约到底算是谁赢?”
她又提起那日拿春宫打赌的事,皇帝想起,轻笑道:“算你赢,那又如何?”
“既然如此,君无戏言,圣上可还记得赌约内容?”
皇帝愣了愣,她抬眼,先一步说出那赌约:“圣上与我定下赌约,若我赢了,圣上便收回那话,并拜我为师……”
“愿赌服输,如今,我算是圣上的老师了。”
“若我当真参加选秀,先有违师德的,便是民女了。”如此一来,若是薄元青不能与她在一起,她自然也没有入宫为妃的道理。
皇帝玩味地一笑,越发觉得她有趣。韩香抬头望向他道:“另外,有些话,民女想单独和圣上说……”
暮色西沉时,两人同乘一辆马车出了宫。韩香枕在薄元青膝上,捏着那张险些闯了祸的肖像细细看,边看还边嘟囔。
“我一直以为师父你只画山水不画肖像是因为不会画呢,没想到画得这样好……师父,我好看么?”
而那人抿了抿唇,道:“不知羞。”
“我知道我好看,我还知道师父你喜欢我,就不知羞!”
韩香笑眯眯地卷起那张肖像放入怀中。半晌,马车中响起那人冷淡的声音:“你与皇上……最后说了些什么?”
韩香抬眼望了他一眼,颊边笑出两个梨涡:“若是师父肯亲我一下,我便告诉你。”
那人皱起眉头,别开脸去。
韩香也不逼他,在晃悠悠的马车中闭上眼,眼前浮现方才情景。

“世人都道多情为风流,可是不知圣上是否明白,世间有种风流,不需多情,却依旧能撩人至深?”
“说起来我其实不擅画春宫,只是擅画那画中人罢了,风流不过是因画中人的风流。想来圣上也不过只是喜欢那样的画,何必一定要做画中人呢?”
是,风流是画中人的风流,从不多情,却偏偏撩人至深。
韩香弯起唇角,猝不及防有一点湿热气息落在唇角,一触便要离开,她抬手揽住那人,将这纠缠加深。
大延城中新开了家画馆,只卖春宫图。主事的女子自己便是个画春宫的一流好手,据说馆中大半画作都出自她手。
画馆开张那日,热闹非凡,有人送来块牌匾。那牌匾上没有落款,不知是谁的手笔,主事的女子却很是尊敬地将它挂起,笑眯眯地打量着,似乎那是什么生财利器,红布揭开后,众人皆仰首,只见牌匾上龙飞凤舞地题了三个金漆大字——画风流。
本文作者:红颜手札(今日头条)
-
Tags: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