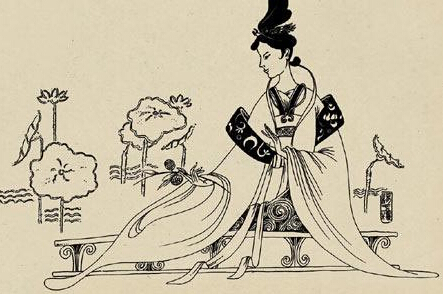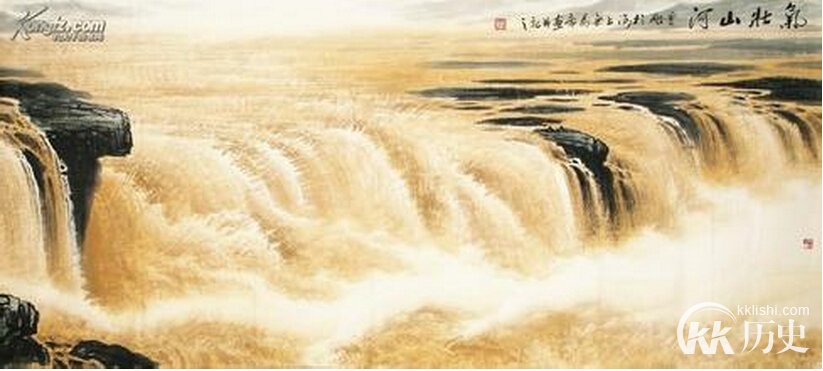北宋第一风流皇帝赵佶:文艺皇帝的“四风”问题剖析!野史趣闻
近日做了一个梦,梦到文艺皇帝宋徽宗找到我,让我帮他写一份“四风问题”对照检查材料,并嘱咐我,一定要深刻,把他玩物丧志、亡国丧身的深刻教训写出来,要做到自我批评辣不怕,别人批评不怕辣。他还红着脸说,自己和儿子赵恒现在被关在东北的荒漠之中,时刻遥望故园,盼望能重新回到故乡,希望能捎信给自己的儿子赵构,励精图治,北定中原,把我们接回去。你放心,我和你哥哥都想开了,不去做那个劳什子皇帝了,我还是写词画画踢足球……

说实话,我对宋徽宗是很有意见的,别人玩物丧志,他玩物丧国。虽说北宋王朝落在他手里的时候,已经是风雨飘摇了,但他要是不折腾,即使中兴无望,但至少可苟延残喘几十年,倘若治国有道,那也不至于出现“靖康之变”那段屈辱的历史了,或许中华文明史可以改写。但是现在,一切都如烟云散去,留下的是对宋徽宗如一地鸡毛般感情复杂的叹息。于是,我在无限的叹息中,为宋徽宗赵佶写下以下对照检查材料,现将材料原文抄录如下。
一、我和宋朝的基本情况。
我叫赵佶,是历史上那个鼎鼎大名的风流帝王。我是父亲神宗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是宋朝第八位皇帝。我当上皇帝或许是命运的错误,我若能预知后来的境遇,打死我也不去做这个皇帝,我还是做个著名词人、画家和书法家好了。
我是庶出,本无希望做皇帝,但是命运给了我机会。实际上,我还是有野心的。我哥哥宋哲宗赵煦八岁开始干了15年皇帝,死的时候只有23岁,连个儿子都没留下。因为我平时守成持重,兴趣高雅,精于绘画书法填词作赋,我的祖母向太后对我的早请示晚汇报也很开心,更为重要的是,我的那些兄弟们个个都不成器,说句自嘲的话,就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祖母就力主把皇帝宝座让给了我,虽然那个可恶的章惇极力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但仍然没有阻挡我荣登大宝的步伐。
我的命运是和我的国家、家族联系在一起的。后来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背信弃义的金国大举进犯,兵临城下,为了锻炼我的儿子赵恒的临场指挥能力,我匆忙间退了位,做了太上皇,我的儿子做了宋钦宗。然而,野蛮是野蛮者的通行证,文明是文明者的墓志铭,野蛮的马背民族根本不吃我们求和的那一套,烧杀抢掠,将我和儿子及大批宫女臣子掳往荒寒大漠,大宋文明毁于一旦,而我和儿子则受尽屈辱,至死未归。
身前事身后名,中国人向来讲究盖棺定论。在历史上我有着复杂的形象。元代那个写史的脱脱对我的评价应该说是公允的,他说我“诸事皆能,唯独不能为君”。事实上,我除了在治理国家方面犯过错误而亡国丧身之外,我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比如我创造的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的“瘦金体” 独树一帜,我创造的“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的工笔花鸟画天下闻名。历史湮没了我的宋朝,但没有湮没我的作品,现在可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土豪们都喜欢收藏我的作品,他们说,赵佶这个人对我们的艺术还是有巨大贡献的。这一点,也许能对我伤痕累累的内心有一些安慰。我还精通骑射、蹴鞠,就是后来世人为之疯狂的足球,虽然我们的足球到现在还是亚洲三流,但毕竟我给世界创造了最疯狂的游戏,也培养出高俅等一批球技精湛但心眼很坏的球星。还有我的词,后世的王国维评价就很高。他把我和那个写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相提并论,并赞扬说我的诗用血写成。这一点上,王国维的评价是精准的,他极为深刻地描画了我当时的心境。从金碧辉煌的京城到荒无人烟的北国大漠,从一国天子到阶下囚,人生的反差何其大也,所以我用血写下了这首词:《眼儿媚》: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我怀念那“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的汴京,这个当时世界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一夜之间沦落于金兵的铁蹄下,曾经的山河万里,曾经的琼林玉殿,曾经“朝喧弦管,暮列笙琶”,“是非成败转头空”,而今是“朝来寒雨晚来风”。

一个强盛的国家,竟然犹如海滩边美轮美奂的沙雕,在一阵疾风暴雨中轰然倒塌。是暴风雨来得太猛烈,是海岸松软的沙子基础不牢固,还是我们的设计缺陷,我不知道。那个可恶的司马光搞了个系统工程,叫《资治通鉴》,让我好好看,从历代的兴衰中,我发现历来的亡国之君无外乎几条,一是皇帝愚蠢而软弱,这一点,我相信我的智商和情商都很高,是金国打败了我,而不是宦官或外戚夺权,换句话说,我是毁于野蛮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冲击;二是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这一点我有些问题,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在我执政期间,有过借改革之名与民争利的情况,但那都是我识人不明用人不当造成的。方腊等一伙人也举起大旗起义,但也只是稍微撼动了我大宋朝的一点根基而已;三是残暴。这一点和我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因为太祖赵匡胤在开国之初,就定下铁律,要把整个宋朝建设成为一个文官政治的典范国家。在我们国家“黄髫小儿,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都是喜欢文艺厌恶战争热爱和平的人民,当时我们大宋朝是世界第一大国,人民安居乐业很和谐。我们不像美国人一样,唯恐世界不乱,我们只想过自己和平发展的日子。但是我应该意识到,极端条件下,和平只能依靠战争获得。在虎狼环饲的西北,死而不僵的辽国,迅猛发展的金国,还有一直被我们压制的西夏,无时无刻不窥视着我们,期待我们犯错。在危机四伏的时代,我忘记了我朝名臣欧阳修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古训,像只鸵鸟,只管把头沉浸在温柔乡里,把屁股留给来势汹汹的敌人,结果导致亡国丧身。
有一点我要说清楚,和我同为文艺皇帝、亡国之君的李煜写过《破阵子》,他说“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他的口气太大了,当年被太祖所灭的南唐,偏安一隅,那才多大的地方,而我们大宋朝,却实实在在可以称得上是万里山河。除了儿皇帝石敬瑭弄丢的“幽云十六州”之外,我们大宋朝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繁荣的经济政治大国。但是我承认,我在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方面用功颇深,但在发展思路上有过失误。对国防建设重视不够。没办法,这是一个王朝的性格问题。男人们提刀上马血战疆场,那是唐朝时候的事情了。那时社会普遍的心态是“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士人往往通过战功获得功名利禄。而到了我朝,来了个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通过调研知道,民间流行的一句话,“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他们还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意思是说,即使是率兵数十万,收复幽蓟十六州,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时的荣耀。在“娱乐至死”的心态下,我朝犹如被抽去了脊椎的巨龙。我朝男人雄性激素明显减退,雌性激素显著上升,失去了尚武精神,人民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流连在花前月下青楼楚馆,在浅吟低唱中送走流光。后世的梁启超说得好,“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致使我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这一点,太祖赵匡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今,我们父子身处尘沙漫天的荒漠,那繁花似锦的汴京仍然经常萦绕梦中,万般愁苦也只能梦中得到慰安。羌笛声起,梦断胡沙,我心中的悲苦之情、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在我这首词里血透纸背。
对于我来说,人生境遇的变化何其大耳。从风流天子到亡国之君,我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淬炼。命运对我的安排是混乱的,我的人生就是一段拧巴的历程。“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一个风流多情的男子,我本可以在大宋朝的安乐窝里做一个吟风弄月的诗人,做一个驰骋街头脚法精湛的足球健将,但是一切如梦如幻如泡影。我最大的教训是,对官场治理不力,使得大宋朝腐败横行,虽然我认识到“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道理,但是我政治立场不坚定,没有坚决打击腐败,反而和蔡京那些腐败分子们同流合污,最终亡国亡身;我最大的悲剧是,身上的文艺色彩浓厚,以为治理国家和我写字画画一样简单;我最大的矛盾是,我是一个想做皇帝但又做不好皇帝的人。
二、我在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大宋朝百姓路线教育活动的安排,我也要参加这次的活动,以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求后世的继任者不再犯我的错误,以使我们的中国永远富强下去,再也不受外族的侵略,恢复汉唐盛世那伟大的荣光。在我执政期间,还存在以下问题。
在形式主义方面,我犯了绝大多数皇帝都会犯的错误。一是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我即位之时,我立志做个“有道明君”。我希望走出宋朝疲软的阴影,恢复汉唐雄风。我派遣王厚消灭了青唐羌政权,收复了自中唐以来已经陷于吐蕃人之手300多年的青唐地区,我派遣童贯远征青唐残部,控制了西域的东南部地区。这一点,我的成绩不容抹杀。但是我身上的理想主义抬头,犯了战略性错误。一心想着夺回河西走廊的战略纵深地带,收回幽云十六州,悍然撕毁盟约,联合金国灭掉辽国,想坐收渔翁之利,结果引狼入室,兵败丧国。在政治路线上,我犯了冒进主义的毛病。后来的法国人托克维尔写了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阐述了政治改革既需要大胆推进,更需要审慎设计的道理。我怀着一腔理想,废弃了持重保守的司马光主义,采取了积极进取的王安石主义路线。但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改革成为臣下腐败借机敛财的手段,导致民怨沸腾。二是自我学习不够,对治理国家经世致用的知识不感兴趣,反而下苦功研究音乐、绘画、书法,存在好玩与有用之间严重脱节的问题。虽然我在发展宋朝的文化艺术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本人在书法绘画等方面成绩卓著,但是存在角色错位的问题。首先我应该是一个皇帝,其次才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我在位时,成立翰林书画院,将画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我精心培养的宫廷首席画师张择端完成了他的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同时,在我的带领下,成立了男子驴球队和女子马球队,在推广蹴鞠即足球事业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我没有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当时主要矛盾是宋朝与虎狼环伺的金辽之间的民族矛盾,或者说是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发展的矛盾。我政治敏感性不强,本末倒置,不去扩充军备强大国防,反而集中精力办书法和绘画事业,在强敌面前,一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尴尬,导致身死国丧。

在官僚主义方面,我的问题特别严重。首先是主观意识浓厚。在干部选任问题上,先入为主凭印象,有感情用事之处。我用人不讲能力,而讲感感情。偏好文艺界、体育界的人才。用了一批喜欢溜须拍马的奸臣,如蔡京等,原来我还以为是六君子,哪想到是六个乱臣贼子。对守旧派,还刻印了“元祐党人碑”,昭告天下,并做出了党人的父兄子弟一律不得在京任职,更不得擅入京师,宗室不得与党人子孙或亲戚联姻等荒唐的决定。其实,我也想重用一些刚正纯良的忠臣,比如被贬谪外地的范纯仁、苏东坡等,无奈他们福运不长,死在回京的路上,真是天不佑我。我喜欢书法,这个天下皆知。身为宋代书法四大家的老贼蔡京就是瞄准了我这个缺点,与童贯一起到处搜集书画送给我,我愣是没看出这种“雅贿”的险恶用心,被他们利用。后来我甚至把蔡京任命为首相,导致六贼当道朝纲混乱。二是缺乏基层调研。我围绕基层一线转得少,围绕青楼歌女转得多。虽然我关爱弱势群体,在京师成立“居养院”,专门收养孤寡老人;在地方州县所在地成立“安泽坊”、“漏济园”,收留无家可归的难民。后来我看了周星驰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苏乞儿对皇帝说,“丐帮有多少弟子不是由我决定,而是由皇帝决定的……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鬼才愿意当乞丐呐”,这句话让我惊心动魄深受震动。我还把兴办学校列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促进了慈善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我深入基层仅限于京师那个小圈子,没有真正走群众路线,为天下苍生服务。自己也曾微服私访,甚至和基层群众打成一片,但那都是京城娱乐界的女明星,如李师师。甚至传出过很多绯闻。而没有真正深入到黎民百姓中间,听民声晓民意纾民困,致使新法走了样,变成了坑民之法。
在享乐主义方面,我为后人诟病最为严重。首先是缺少担当,贪图安逸。我追求“丰盛、通达、安乐、阔气”的生活,渴望在大宋建立一个“丰亨豫大”的太平盛世。在这种享乐主义的指导下,我穷奢极侈,滥增捐税,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园林,铸九鼎、建明堂,令童贯在苏州、杭州设立了“造作局”,集中东南地区的数千名工匠,制造各种工艺品;令朱勔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从东南地区搜罗各种奇花异石,用船经大运河运往汴京,《水浒传》里说的“花石纲”,就是献给我的奇珍异品。

我缺少在关键时刻敢于担当的勇气,在金兵南下进攻汴京的时候,慌忙传位于赵桓,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我自称“太上皇”,带着蔡京、蔡攸父子一路南逃。哪想到我那儿子也是个软蛋,几次乞和不成,最终身败国灭。第二是在世界观上出了问题,沉迷于追逐声色寻花问柳之间。我命人在宫内设立市肆,让宫女当服务员卖酒,我装成叫花子行乞其间。我设置了行幸局,专门为我打点出行游乐之事,后来我干脆微服出宫,游走于妓院酒楼之间,整日和李师师等美女厮混,最后输了人生玩掉了国家。
在奢靡之风方面,我还存在很严重的问题。首先是执行规定不够坚决。对祖上定下的一些好政策,没有始终坚定地执行,破坏了政治制度的严肃性和政策的一致性。我改变了宦官不得为节度使、领兵主持军政的政策,改变了外戚不任军相、宰执应避亲嫌的制度,使蔡京、蔡攸父子先后担任宰相。为了偷懒,我让宦官代行御笔,破坏了宋朝的诏令颁发制度,造成朝政极度腐败。我丧失了诚信从而丧失了国格,在与邻国的谈判中经常出尔反尔,导致好多条约成为一纸空文。二是参加与工作无关的应酬较多。放弃自己九五之尊的身价,对有的臣属热心、热情地提供一些生活之便、健身活动、请吃、馈赠等,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蔡京的儿子蔡攸,这个人很会来事,很讨我的欢心。还有那个长得很帅能歌善舞的宰相李邦彦。我经常和他们几个宴饮狂欢,插科打诨,不醉不归,以至于“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 。
以上是围绕四风问题,对我进行的一次“触及灵魂”的剖析。最后,我想表达个人的观点,就是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这些关乎我的历史地位,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第一,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宋朝。历古以来对宋朝的评价褒贬不一,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事实上,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兴学重教,政治上较开明廉洁,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繁荣的时代。但也有人说宋朝是中国历史军事软弱的时代之一,经常被游牧民族辽、金、夏欺负。其实,把眼光放远一点看,我们就知道,宋朝的灭亡完全是冷兵器时代的悲剧。就像罗马人征服古希腊文明、波斯人征服埃及,后来的蒙古人征服我们的南宋一样。虽然我们的实力要远远超过金、辽,但在冷兵器时代,经济与技术的进步似乎与胜败没有直接关系。往往都是野蛮民族战胜先进民族,这一点,我作为亡国之君,似乎是历史的选择,是命运的倒霉蛋。最后是对我个人评价的问题。我在四风问题上是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的主流是好的。我说过,我最大的错误在于用人不当和纵容腐败,这也是泱泱大宋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
本文作者:好玩的国学(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