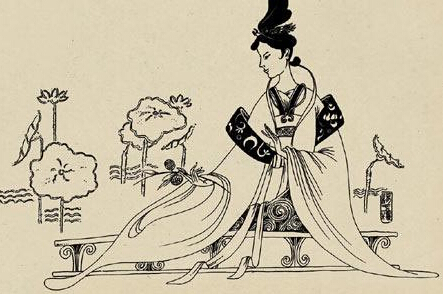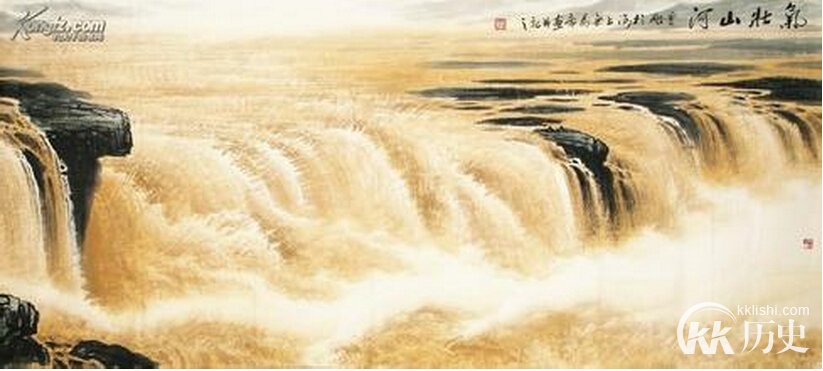浅水喧哗的诗意流动野史趣闻

树
郑敏
我从来没有真正感觉过宁静
象我从树的姿态里
所感受的那样深
无论自那一个思想里醒了
我的眼睛遇见他
屹立在那同一的姿态里
在它的手臂间星斗转移
在它的注视下溪水漫漫流去
在它的胸怀里小鸟来去
而它永远那样祈祷,沉思
仿佛生长在永恒宁静的土地上

浅水喧哗的诗意流动
雪莱的诗歌读过两个译本,一个是穆旦的,也就是查良铮,他和查良镛算是一族之中的远房兄弟。看起来好像亲兄弟的两个人,虽都是源于海宁望族,天南地北,金大侠与他也没有见过面。
译诗的高明者,非诗人不可。穆旦开始从事外国诗歌翻译的时间,大抵与沈从文开始古代服饰研究的节奏,文人的心思流淌,几乎相同。罡风浩荡,白驹过隙,敏感的他们,也唯有感慨。
无论是喜悦或悲伤都会溜走:
我们的明日从不再象昨天,
唉,除了“无常”,一切都不肯停留。
另一个版本是江枫的,江译本在查译本之后才出版,各有特色,出版过程一波三折,对雪莱诗歌感兴趣者甚众,包括郭沫若,曾想分一杯羹。由于江枫的固执,此事作罢,之后雪莱译诗百花齐放。

据自己个人阅读喜好,江译本有点坚硬偏于激昂,类似那首著名的《无常》,结尾那句,宣言铿锵的意味超越了人生无常的萧索,“人世间的明日绝不会雷同于今朝,万古不变的,独有无常。”
英诗磕磕巴巴读起原文,目前而言,难以融会贯通拜读原诗,所幸两种翻译比照着读,倒是很习惯了。过去读到“吻是灵魂与灵魂相遇在爱人的嘴唇上”,霎时不知所往,其间心潮澎湃远比《西风颂》。
当然懵懂少年还不能体会《西风颂》的壮怀激烈,只有等待诺干年后,少年老成,厌倦了生活的重复,才可能萌生“打破旧世界,追求新世界”的念头。此时也好过,如今我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中庸。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这是穆旦去世前的《冥想》,查良铮将“查”姓上下拆分,“木”与“穆”谐音,得“穆旦”之名。夕阳西下,秋意渐浓,普通的一天,将要开始黑夜,“生活是痛苦的白天,死亡是凉爽的夜晚”,而喧嚣远没有结束。

现存于世的雪莱写的最早的一首诗是《猫》,那年诗人八岁,骄傲的天才。八岁的他在诗中以罪人自居,还写出了“你们不容易猜得出,折磨这世界各住户,所有各种样式的痛苦;和像魔鬼一样的,从可怜的灵魂降生起,就伴随着它的灾难和邪恶”这样深沉的句子。
穆旦似乎把其诗里的玄机,藏于诸多雪莱译诗之中。他把看起来那么表面、具体的字句,兜在一起,突兀地组合出超越现世平凡,抽象而富有哲思的诗歌之美,读来依旧充溢着无数可能的暗示。
后来去沪上出差,徜徉于福州路的新华书店,至今还记得邂逅《九叶集》时的阳光灿烂。那是第一次阅读穆旦以及他们的九叶诗派,上海的秋天,是个有点势利的小家碧玉。

抗战胜利彼时,西南联大回迁,平津的诗歌文学趋于繁荣。辗转聚集于上海的辛笛、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等等,创办刊物,与平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渐渐形成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转移到现代主义的诗歌写作。这大概便是九叶诗派的雏形。
他们无一例外的崇尚外国诗人,除了穆旦受雪莱影响,杜运燮引奥登为知己,女诗人郑敏与冯至一样,对里尔克刻骨铭心,年长的辛笛,颇得印象派艺术精神,在那些色彩斑斓的光影变幻中,寻觅古典与现代的交融。
九叶诗派诸人开始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穆旦之于雪莱,其代表作是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诗风气势磅礴,难怪江枫译诗的格调,这恐怕亦是误会。纵观雪莱长诗短诗,豪放婉约兼而有之,铿锵的感伤也在所难免。
英国浪漫主义运动黄金时期的三位年轻夜莺,拜伦,雪莱,济慈,无一例外的早逝,拜伦说《我看过你哭》,可惜我未哭,雪莱的《无常》,“趁天空还明媚,蔚蓝...等醒来再哭泣”,济慈的《但愿一星期能变成一世纪》,或许真的”短短的一岁就变成一千年”。

【绘画:伊凡·伊凡诺维奇·希施金(俄罗斯)】
本文作者:菩提恶之花(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