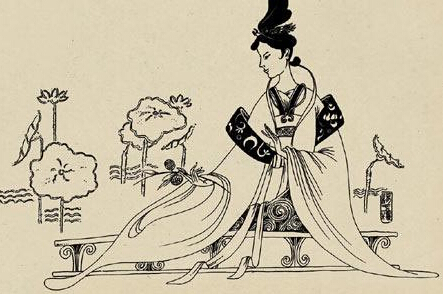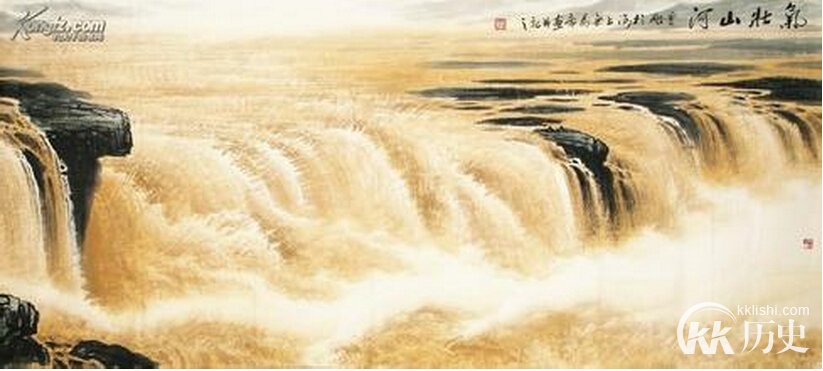《顺天时报》将五四运动定性为“骚乱”野史趣闻
《顺天时报》对五四运动的报道,有很多是关于北京大学“内哄”的报道,以之证明该报“阴谋论”的正确。如6月9日,该报报道称北京发现了“惑乱人心传单”,从新世界楼顶“约有数百张,飘然飞舞而下”,传单内容是代表北京市民要求处决卖国贼云云——这自然便是陈独秀身穿白西装散发,并导致陈被捕入狱的那叠传单。
“五四”是一个“众声喧哗”的空间,这已是研究者的共识。可是,出于意识形态需要或立场所限,被关注、讨论得更多的,还是“进步”的那一条线。
这种倾向其实也是“古已有之”,1919年9月出版的《五四》一书,由北大学生蔡晓舟、杨量工编辑。内中第四章“舆论”,收各方文字甚伙,但比较缺乏的,一是执政的皖系言论机关的评述,一是日本方面的舆论,总之,“反派”的意见处于缺席的状态。
但是,缺席者也可以是“缺席的在场”,《五四》的编者,并非不知道或不关注反方的观点,他们只是通过选取与之针锋相对的舆论,构成一种隐性的批判。譬如,这一章中选载《日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博士之论文》,并注明“中日各报多载之者”,便可以视作对日本政府舆论的某种回应。
这位“吉野博士”,想来是从报章上了解五月四日事件的,其中有些细节,未免传讹,如说傅斯年是北大教授,又说陈胡钱傅“四教授”被政府免职等等。不过吉野博士的观察是从“文明”、“进步”为着眼点,他除去遗憾于“彼等之手段,颇极狂暴,而未尽文明”之外,主要是赞颂“北京大学学生之开发,至于如此其速,颇与日本之开明思想由民间而渐入官立大学者,有相比类之处”。因为“官立大学”,一向被认为是保守官僚的养成所,而“开明的自由思想”,向来在中国南方盛行,“今以官立大学之学生,于中央政府所在地,而鼓吹自由思想,极热烈极彻底”,这与日本十年前的状况很相似,作者为此感到“吾人不得不为东洋文化发达贺也”。
吉野身为日本民间学人,不妨表达个人对北大开明思想的欣赏,但关系到此次运动的“排日”性质,他不能不细为辨析——这种辨析的背景,便是日本官方舆论对五四运动的强烈指责。
5月21日日本公使小幡酉吉自中国外交部提交照会,内容主要是指责中国社会的反日言论,并再三要求中国实行言论管制:“对此荒唐无稽无政府主义之主张与阻害友邦邦交、挑拨两国国民恶感之言动,不加何等之取缔,是本公使之甚所遗憾者也。”

小幡酉吉
官方交涉是一方面,说到舆论战,日本政府在华的代言机构,但是鲁迅评为“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那份《顺天时报》。
《顺天时报》是日本外务省的中文机关报纸,自然“诸事为日本说话”(周作人),但一份现代报纸,说起来总是代表着文明进步的言论机构,它也有自己先天的立场限制。面对本身就负载着多重意义的“五四运动”,《顺天时报》的姿态并不像小幡酉吉的照会那样简单决绝,也不如后世的二元叙述之中那样面貌清晰。

《顺天时报》
在1919年5月之前,《顺天时报》对北京大学的新思潮新文化,一直持正面肯定的态度,如称赞蔡元培长校以来,北京大学“形式上精神上大有可观”,陈独秀则“中西学问均优,办有某英文杂志,其生平著述颇富”。在以林纾为对象的“新旧思潮论战”中,《顺天时报》也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一边,指出“关于思想问题,常分为旧型保存论者与破坏论者两派,而保存论者往往借政府之权力或社会的威力,以图压抑破坏论者。然权力的压抑往往失败,或足召社会之紊乱”,希望“有权者及为政者最宜注意”,并称赞新思潮是“社会内省的苦闷之声,其或将见社会的向上之曙光欤”。——基于《顺天时报》的这种立场,《每周评论》在汇集各报舆论时,收入该报的四篇文字,无不是一副对新思潮乐观其成的姿态。
《顺天时报》对五月四日事件的定性是“骚乱”,不过,它与它代表的日本外务省,都不愿意承认五四街头运动是单纯的排日运动——这一点,前述吉野博士的文章也持此见,日本官方、民间舆论的区别,在于吉野认为这场运动“纯然为自发的,并无何人煽动其间”,而《顺天时报》等日本报纸“照例载称某国之煽惑”,换言之,是将学生运动与国际利益争夺、国内政治争斗相勾连,将运动的动机阴谋化。

五四运动时上海女学生示威游行
这个“某国”,指的便是美国。一战之后,日本在远东的主要假想敌,便是美国。五月四日之后,《顺天时报》的假想敌,便是有美国背景的《益世报》。5月23日,《益世报》因发表山东第五师的集体通电后,被京师警察厅查封。《顺天时报》更是连日有新闻或评论攻击学生运动后的“暗幕”:“此次学生藉争青岛问题演出是等风潮,其内幕为野心政客及亲某派所怂恿,并闻此派阴谋家非但利用青年学子以困政府,且有勾连军队及劝诱商人罢市为学生之后援。”
《顺天时报》根本不承认日本对中国的领土、主权有任何非分之想。6月10日,《顺天时报》刊出《日人论调二种》,声称关于山东问题,日本国民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曰山东问题宜全行抛弃日本之主张,望专管居留地固无其必要,即铁道矿山之权利,亦无须获得。”另一种则主张“条约上之权利固不可不保持之,然中国人既扶持疑念,则声明交还之外,于交还之时仍不可提出不当之条件”。“编者按语”强调“此等议论实与日本政府所执方针一致,且为日人多数之意见,即可视为日本之舆论也”。
《顺天时报》也不承认以它为代表的日本报纸对中国有何敌意:“中国人先怀成见,对于日人所有之言论,均以为欺罔中国,祸害中国,诚为大不可也。”面对中国舆论界的猜忌与反感,它还是强调报纸作为言论机构的公共性:“须知执笔于日本第一流之新闻者,在思想界多为先觉之士,莫不有指导国人思想之抱负,故关于对华关系之持论,多为进步的,较诸一种记者徒以离间他国之国交,或紊乱他国之秩序为目的者,实不可等量齐观也。”
一方面替日本撇清,另一方面则是不遗余力地攻击“某国”,如6月7日报道《学生有发财者》:“昨日有北京某大学预科学生某甲年十六岁持现洋二百元示人,询其钱何由而来,则答云系系某国公使馆所给,有分得五十元者,有分得百元及数百元不等云云。”
《顺天时报》对五四运动的报道,有很多是关于北京大学“内哄”的报道,以之证明该报“阴谋论”的正确。如6月9日,该报报道称北京发现了“惑乱人心传单”,从新世界楼顶“约有数百张,飘然飞舞而下”,传单内容是代表北京市民要求处决卖国贼云云——这自然便是陈独秀身穿白西装散发,并导致陈被捕入狱的那叠传单。
与这条新闻一起的,是“京师警察厅启事”,称接到“北京大学全体学生邮函”,指责传单内容“全属义和团之谬见,学生等深受教育,岂有作荒诞思想之理?”这种传单“为奸人暗布,别含用意,或为宵小造谣,以利私谋”。
《顺天时报》于6月13日制作了一个“关于学潮之四方八面”的专题版面,主要内容是以部分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在校生的名义,向政府交递的反对学潮的呈文。如北大毕业生“郑滋蕃缪承金杨绪昌周蔚生成林等三百四十九人”的呈文里说:“北京大学自蔡孑民先生长校以后,新旧文学党派分歧,在蔡校长并取兼容,原期并行不悖,而邪说传授,祸基已伏”,因此酿成风潮,“滋蕃等先后毕业北京大学,关怀母校,义不容辞”,要求政府尽快平息风潮。
而“北京大学学生任玉枢郭士恂王显模等八百五十六人”,以在校生身份指证“藉端煽惑恣意肆行少数专权托名全体,此固学子恒情,而敝校尤甚”,在他们的叙述中,“自蔡校长辞职远适故乡,罢课挽留,已非众意,积日经旬,倍形纷扰,坐荒学业,虚掷光阴,或届期满欲试不能,或被强从欲归不得,横行独断莫可如何……”
《顺天时报》还报道说,学界的内哄越来越厉害,“自二次讲演之后,各学校学生因避风潮出京回籍者,竟达十分之四”。
这些摘引、报道与评述,真伪大可进一步考究。揆诸情理,对于长时间的罢课、游行、集会,以北大之大,肯定不会全无异辞。只是,媒体选择什么,报道什么,其实背后隐伏着自己的立场、利益与目的。后世的观察者,无法真的“复原现场”,但过眼不同来源的材料,总能让人对于历史的复杂纷乱,了解得多一些,更多一些。

本文作者:杨早讲史(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