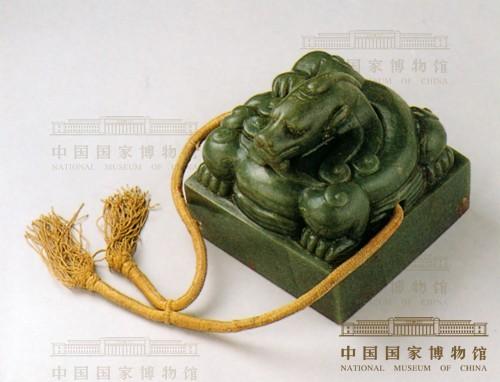公然造反叛大清野史趣闻
公然造反叛大清
人在北京的乾隆帝心惊肉跳,马上命令班第在途中逮捕阿睦尔撒纳。但是,班第手下只有500士兵,而仅伊犁一处,就有喇嘛6000多人,这些人基本都是阿睦尔撒纳以银两买通的心腹,加上阿睦尔撒纳的旧部和阿巴噶斯等宰桑、台吉及其部下,阿睦尔撒纳能够调动的兵马至少有一两万人,所以,班第根本不可能在当地擒拿阿睦尔撒纳。
逮捕不了阿睦尔撒纳,班第就一直催促对方马上动身到热河入觐。只要到了热河地界,以几个戈什哈之力,就能把阿睦尔撒纳收拾了……
计划赶不上变化,一路行进一路等,到八月中旬还未见到科尔沁额驸给自己的回音,阿睦尔撒纳深知事情有变,就于八月十九日忽然率众潜逃。
当时,他跟随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行至乌隆古河附近,那里距他在札布堪河的昔日游牧地不远,地形熟悉不说,又有旧部在附近接应,于是,撇下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他就从额尔齐斯河间道向北逃逸而去!
阿睦尔撒纳公开反清后,其手下党羽纷纷作乱响应。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清朝的定北将军班第、参赞大臣鄂容安、以及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三人,得知情势大变,就带着手下寥寥可数的500兵士,慌忙从伊犁河北的驻地出发,匆匆回撤。
撤退途中,准噶尔叛军紧紧追赶。二十九日,一行人跑到距伊犁二百余里的乌兰固图勒,即被叛军追及包围。
当时,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见敌兵势大,不听鄂容安劝告,即刻扬鞭拍马奔逃。那500兵马,见其中一名主将跑了,也多随之而逃,一下子就把班第和鄂容安撂旱地里了。当时,这二人身边,只有司员和侍卫60人!
面对多达上万的准噶尔贼军,班第、鄂容安及其手下力战不支,二人相顾叹息道:“今日我们真是白死了,于国事无济,辜负圣上嘱托!”
叹息久之,班第拔剑自刭;鄂容安也抽剑欲图自杀,但他是翰林出身,腕力弱而不能致死,于是命仆人用刀猛力刺戮自己的腹部,血流肠溃,终于得死。

鄂容安
班第乃蒙古镶黄旗人,鄂容安乃是满洲大学士鄂尔泰的儿子,皆为乾隆帝心腹大臣。如此,清军一主帅、一大臣被包围自尽,成为近百年来清朝罕有之事。两个如此刚烈的蒙古、满洲大臣,确实耿耿忠臣,乃真正的大清英杰。到了清朝中后期,满蒙权贵中这样的人就非常罕见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时期,清朝的满蒙封疆大吏,基本上都是闻警即逃。
班第和鄂容安死后一个多月,乾隆帝才得二人“陷敌“的消息,但当时还不知道二人已经自杀殉国。为此,一直强调清朝文臣武将要为国捐躯的乾隆帝,罕见地告谕军机处,让他们设法和班第、鄂容安联系,希望二人静待时机,可以不死:
“以朕初意,准噶尔危乱之余,甫经安定,若屯驻大兵,恐多惊扰,是以但命伊等驻扎办事,兵少力弱,为贼所困,非失守封疆可比。伊等或相机脱出,或忍死以待大兵,方为大臣举止,若谓事势至此,惟以一身殉之,则所见反小类。鄂容安素称读书人,汉苏武为匈奴拘系十九年,全节而归,阿睦尔撒纳固不足比匈奴,我大清又岂汉时可比,自当爱惜此身,以图后效。恐伊等以失守罹罪,不识大义,遽尔轻生。”(《清高宗实录》卷499)
一直要臣子保持忠贞气节的乾隆帝,之所以罕见地希望二位臣子不要自杀殉国,其实正是因为乾隆帝深知正是自己一人,才是导致阿睦尔撒纳叛乱、陷二臣于敌阵的“罪魁”!
日后,班第、鄂容安灵柩回京,乾隆帝亲临祭奠,并且把两个当时生擒的、导致二臣丧生的贼酋克什木、巴朗抓到灵前,活生生割耳砍头祭祀。为了羞辱陷贼而不能死义的萨喇尔,乾隆帝还命令这位倒霉蛋跪在灵前观看整个祭祀仪式。
在商讨谥号的时候,清廷内阁由于鄂容安是翰林文人出身,按照常例,谥号中都有一个“文”字,所以,就拟了“文刚”、“文烈”两个谥号呈乾隆帝选择。悲痛不去,乾隆帝以朱笔抹去两个“文”字,赐谥“刚烈”——为清朝死节文臣开了一个先例!同时,在乾隆帝亲拟的赞语之中,还有“用违其才,实予之失”之语,深自疚责,可见他对于鄂容安的爱惜和对他英才早逝的遗憾……
当然,最终造成阿睦尔撒纳造反、伊犁地方准噶尔部落趁乱反叛的结果,班第、鄂容安确实也有失误之处。特别是班第,气量窄狭,谨慎过当,一直没有妥善慰抚准噶尔投降的大小头目。为了避嫌,他平时也不和伊犁附近的部族首领来往,和当地豪酋关系极其疏远;鄂容安翰林出身,虽然久在军机处、上书房行走,又历任巡抚、总督,但他其实对于行军打仗根本就是外行,又不通蒙古语,所以,人在伊犁,鄂容安并不能展其所长;萨喇尔作为准噶尔人,身为定边右副将军和一等公爵,很能打仗,但这个人原来不过是达什达瓦台吉手下一个宰桑,在厄鲁特四部内部根本就没有威望。他以清将身份到伊犁之后,又妄自尊大,惹得从前比他地位高好多的准噶尔部众台吉和宰桑心怀怨恨。
这三个人,有文有武,民族不同,性情各异,在伊犁也没能做到同舟共济,加上疏于自卫,一朝事起仓猝,三人只能孤军奋战,最终二人自杀军溃,也在清理之中。
本文作者:赫连勃勃大王(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