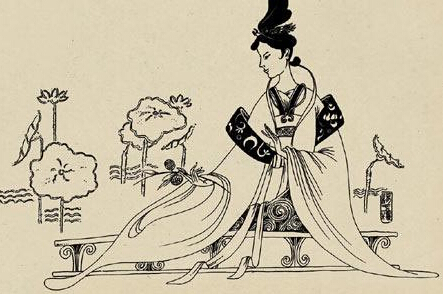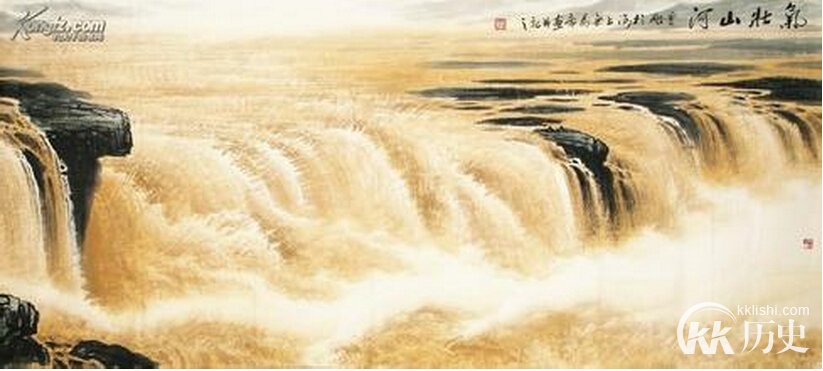「传奇」荒墓冤魂(二)野史趣闻

当他回过身来看时,只见这棺材里露出一个头来。那头发黑黑的,插满了珠翠,脸看不大清楚,轮廓却很秀气。贾东门稍稍定一定神,气也均匀了许多,见动静不大,便朝那木棺走去。
一会儿,那棺木内的人站了起来,竟是一个标致的女子。借着月光,贾东门渐渐看清了,除了面色显得有些苍白,眉眼却十分周正媚人。出得棺来,女子在东张西望,似乎像一个迷了路的人在寻找出路。
贾东门见是女子,胆子登时大了许多,心想:管她是人是鬼,且试她一试,便问道“那一女子,你是什么人?”
他这一问,女子才发觉有人在这里,吓得将脸捂上,道“你是何人?”
贾东门答道“娘子不要害怕,我是好人。刚才路过此地,见娘子从棺材里出来,不知何故,特上前来看个究竟。娘子,你到底是人是鬼,可否告之?”
听贾东门这样一说,那女子才放下手来,又见贾东门虽然长得不俊,却也像个朴实的人,便如沙漠中偶见人迹一般,有了一腔亲切之感,未曾开言,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便向贾东门讲述了自己的遭际。
原来,这女子郑王氏乃是附近南台镇成衣店店主郑阿光之妻。前不久,她闹了一场大病,遍寻名医,也不见起色。因为丈夫阿光远行做买卖,膝下又无儿,只靠小叔请医熬药。幸而小叔郑阿毛极懂孝悌之礼,照顾十分周到。那日吃过药,昏昏沉沉便睡了过去,不知怎地,竟从棺木里出来,真像一场梦。
贾东门听郑王氏这一说,心里托了底,知道确实是个活人,便完全恢复了神志,见女子娇滴袅娜,煞是可爱,不禁放出大朵心花,道“想必是娘子病重,家人误以为死去,便埋葬了。”
郑王氏一想,甚觉有理。如此看来,面前的竟是救命恩人了,也没及细想他是如何想起掘墓开棺的,便施了一礼,道“恩人在上,请受奴家一拜。”
贾东门浪荡二十多年,从没有人正眼看觑过,今这美貌娘子竟给他施这样的大礼,乐得他犹如驾雾一般,忙拉起郑王氏。在两手相触的一刹那,贾东门觉得这女子玉葱般手指虽有些凉,但软软地像面团一样,不由心旌荡漾起来,拉着的手再也不愿松开。
郑王氏见贾东门拉着自己的手不放,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忙道“恩人的大恩,奴家没齿不忘。人言,救人需救活。就烦恩人将奴家送回家去,奴家必有厚报。”说罢,挣脱双手,移步便走。
贾东门见状忙道“娘子且慢,你家对你未死即葬,无情无义,回去做什么,不如随我走罢了。”
郑王氏道“我夫经商在外,不知这场变故;小叔仁厚,孝悌双全,也不知奴家会起死回生,我今回去,全家都会大喜过望,也会感念恩人的厚德的。”
贾东门见郑王氏执意回家,就显出了本来面目,涎皮涎脸道“你既称我是恩人,就该以身相报,何况郑家皆以为你已是死人,即便跟我走也没打紧,如何这般固执?你莫不是嫌我贫贱?告诉你,我如今已是腰缠万贯的大老爷,保你今生今世享用不尽。”说罢,解开上衣,露出腰间的银带。
郑王氏见此人言语十分不着调,且又行为轻佻,知是遇了小人,便委婉言道“恩人哪里话来?奴家自幼读书,略知大礼,救命之恩,怎样报答也不为过。只是奴身已属有主,且夫郑官人尚健在,如何便自行委身他人?除此一项,其余如何报答皆可。”
贾东门见郑王氏心如铁硬,软来不行,便沉下脸来“实话告你,今天你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你来看”说着,便指向伍昌尸体,“这人便是我杀死的。本想放进你的棺木,不期碰上你死而复生。你若不从,一根绳也结果了你,仍做你的死尸去。”
郑王氏这才恍然大悟,万没想到才脱死运,又遇阎罗,早已浑身筛糠一般抖个不停,自己一个弱女子,在这漫荒野地之中,如何逃得过恶狼的吞噬?不如暂时答应,再见机行事。于是,对贾东门说“既是如此,奴家随你去便是。不过,须待远走定居后,明媒正娶方可。”
那贾东门乃市井无赖,如何不明白这是缓兵之计,便虎着脸道“你我既已是夫妻,不必理会什么媒不媒的,就在这里行夫妻之事吧!”说罢,便扑上前撕扯郑王氏衣服,郑王氏见状,已是魂飞胆丧,周身无力、一个好端端良家妇女竟在此时此地被恶棍奸污了,哭都没人回应,甚至没有想到,经此一难,自家也觉无颜见亲人,只得任恶狼摆布,随他远走,听凭命运把自己带到何方。
再说郑王氏这边。郑王氏之死,正是江苏夏季,阿毛怕尸体腐臭,一面急急埋葬,一面教成衣店伙计去南方向哥哥报告嫂子的噩耗。这一切都忙完,才又教人通知郑王氏娘家。
郑王氏之母王陈氏得到丧讯,忙带了儿子王瑞赶来吊丧,听阿毛讲女儿已埋葬,便买上香烛祭品,由阿毛陪同,到郑王氏坟前哭祭,想到女儿如此年轻便命丧黄泉,如今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王陈氏悲从中来,哭得异常哀切,王瑞想念姐姐平日的亲善呵护,也哭得死去活来,阿毛则陪着又掉了一回眼泪,又想到此时长兄尚不知嫂子离世,将来自己如何向长兄交代,更觉多一层悲哀,于是由陪哭变成号啕大恸,弄得王陈氏和王瑞反过来相劝,直哭了半个时辰,方才罢住。三人相携,接过伙计们递过的锹,为郑王氏培土。
王瑞正欲往坟头上培土,突然发现坟堆背后有一条发辫半埋半露,觉得好生奇怪,他蹲下身去,小心翼翼地将发辫拽出来,见是一根辫稍齐整,根部却散乱不齐的半截辫子,更是大起疑云,回头唤母亲。
王陈氏见了,一种不祥念头笼罩全身,她原就有些怀疑,认为女儿病得突然,病程又极短,埋葬也如此急草,女婿又恰恰不在家,但听了郑阿毛说明,倒也无法说出什么,只是疑团不肯散去而已。王瑞一呼唤,她那未散疑云又顿升心头,她弄不明白坟土上何以会有男人发辫,且又只是一部分,极像是被拉断的,一时血涌上来,厉声质问起阿毛来:“这坟土上的发辫究竟是怎么回事?”
阿毛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形弄得如入云里雾中,一时竟将答不上来、嗫糯道“我也不……晓得……这……”
王陈氏见状,像是看到了不祥的预感得到某种证实,用双目剑一般地指向阿毛“这里有鬼儿!我说呢,女儿好好的怎么就突然没了!况且正是在女婿出远门的时候!郑阿毛,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阿毛为人老实,此情此景竟吐不出半句,他哪里知道贾东门在草草掩埋伍昌时,根本不管什么发辫不发辫,胡乱堆上土便逃之夭夭了。其实,王陈氏也不曾细想,即或女儿是被阿毛害死的,何以会有男人的发辫出现在这里?不过,做母亲的在失去儿女的突变时刻,却是会丧失理智。
王陈氏见阿毛不语,似乎都明白了,立即怒发冲冠,劈胸将阿毛拉定,连哭带喊“你还我女儿,还我女儿来!”
倒是王瑞有几分冷静,拉住母亲,道“请母亲暂且息怒,待把事情弄清,再理会不迟。”王陈氏一想也有道理,即放开了手,问阿毛道“我女儿得的什么病?为何没知会给我?人死了为何不等我们来便下葬?你今天说不清楚,别道老娘翻脸无情!”
阿毛觉得这老妇人好生蛮横!先前都已经告知过,如今又要问来,分明是想抓我把柄,寻事于我。可又一想,既然不问发辫而问起女儿,这便没甚打紧的了。于是,从容道“兄丈母大人在上,嫂子的病及过世情形,昨夜已然察过。嫂子得的是急性腹症,我兄不在家,是我请的郎中,并亲自抓药熬药,细心侍奉,不意病来得既急且重,只几天便已无脉,是郎中对我说人已过世。本想知会兄丈母,奈何天气过热,尸身已有异味,怕挺不过丈母大人来到,故做主安葬了。这一切有郎中及家中下人等作证,俱无诈讹,更无其他枝节,只是发辫一事,晚辈亦不知就里。不过,下葬时并不曾有过……”这阿毛确实忠厚,又提到了发辫,一下又挑起了王陈氏的怒火,她接过阿毛的话头,道:
“既是无人知晓的怪事,那么就将坟墓掘开,若是我女儿无异,便各自无干,如是有异,定不与你干休!”
阿毛对开棺验尸并无畏惧,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于是就近借来锄杠等用具,刨起坟来。周围招来了不少看热闹的,都想看看这桩新鲜事。
坟本是新坟,加上贾东门又刨过一回,土十分松软,不足半个时辰,棺木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见棺木漆色犹新,是口上好的寿材,但棺盖有些歪斜,似被动过。果然,当阿毛用撬杠要去撬时,发现盖是浮掩着的,并无棺钉锁住,只轻轻一移,棺木里的人即敞露在众人面前。
此时,王陈氏、王瑞、阿毛以众围观的村民俱围拢过来,探过头去观看。众人不看则已,一看之下,都大吃一惊——棺木里躺的竟是一个男性尸身!但见那具尸体歪歪扭扭地侧在棺内,脸上满是血污,双目突出,脖子一道重重的勒痕,衣服上泥土斑斑,发辫只有尺把长,下梢散开,这正与坟堆上的对上。
最吃惊的是阿毛,他简直傻了一般,不知道这被人凶杀而死的男子是谁,又何以钻到嫂子棺木内,嫂子又哪里去了,惟有目瞪口呆的份,哪里出得半点声音?
王陈氏与王瑞却在恐怖过后,一齐向阿毛扑来“还我女儿”,“还我姊姊”不迭声地吼着,用拳头没头没脸地砸将过去,阿毛从呆怔中一下又进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一边遮挡着,一边后退着,一边大声喊道“不要打了,听我说,听我说……”
围观人中有为王陈氏母子助威的,有帮助打阿毛的,一时乱做了一团。这里正自扭做一堆,忽听一声大喊“都给我住手!”声如雷炸,把这一干人唬得都歇了下来,朝这声音望去。只见那人高大魁梧,像个做公的差役,见众人罢了手,便道:
“我已在此观看多时,你们且慢动手。此事好生蹊跷你女儿死不见尸,固是一疑;可这男尸又是何人?为何人所害?害死后为何又停放你女儿棺木里?你女儿尸身又哪里去了?这些都没弄清楚,先自乱打起来,成何体统?”
阿毛见有人说公道话,方才稳住了神,向大汉一抱拳,拱手说道“这位公爷说得正是。在下确实亲手葬过嫂子,不知如今为何是这般样子。这一男尸,在下并不认识,也正自不解,要在下承罪,实属冤枉……”
王瑞抢道“我且问你既是冤枉,可敢随我母子同去公堂,请青天大人裁断?”
阿毛见王瑞要拉他见官,也动了气,道“见官就见官,心里没鬼,谁还怕你不成!”说罢,彼此扯袖揪胸,朝南台镇地方里衙走去。那大汉实是东台县衙差,到南台镇行公,恰遇此事,有经验,便吩咐找地保派人保护现场,而后随围观众人并王陈氏一行,迤逦向前拥去。
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秋困桑与萧萧某(今日头条)
-
Tags: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