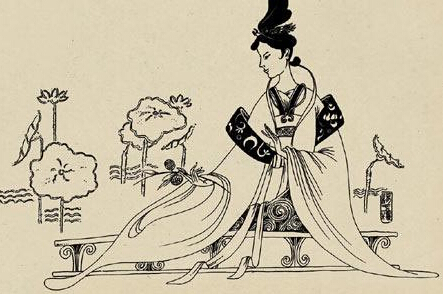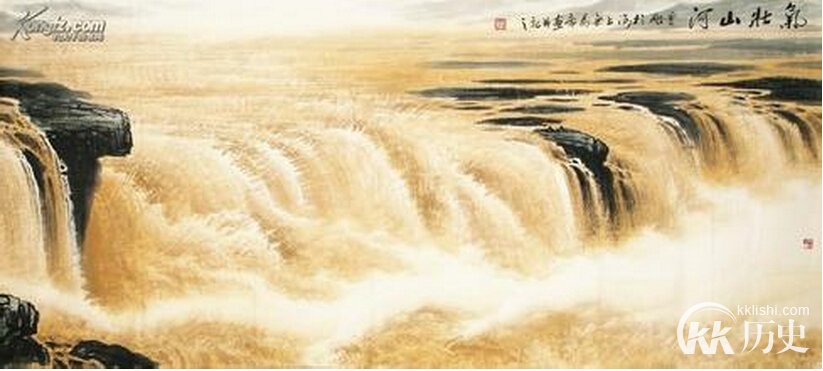红军娃娃传令兵野史趣闻
红军娃娃传令兵
———101岁老红军涂龙琛的中央苏区战斗经历
□特约记者 王坚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长汀县涂坊镇涂坊村坝沿边,一座体积庞大、建筑精美的客家古围屋坐落其中。围屋北门内侧墙壁上,至今留存一副诫示子孙后世的经典古联。在风起云涌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这座沧桑百年的古宅中,先后走出了数位红军指战员。今年101岁的老红军、原中央苏区福建军区司令部特务连通信兵涂龙琛老人就是其中一位。
老人精心保存着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岁月积淀的生命荣光使老人益发神采奕奕。远逝的烽火生涯,凝固成无数珍贵的记忆底片,在初夏的阳光里放大、显现……

“朱毛”红军的“纸壳名片”
涂龙琛于1918年8月16日出生,父母亲都是地道的农民。1929年5月20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途经涂坊,涂家兄弟从此和红军结下了不解之缘。长兄涂冠琛参加张赤男、罗化成领导的汀南暴动,后编入红四军第11师,1932年在攻打赣州战斗中牺牲。
“朱毛红军到涂坊,我才11岁,跟着大人上街看热闹。红军在涂坊开展群众工作,毛泽东在赖屋坪的台子上讲话,叫大家不要害怕,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有东西就卖给红军吃。那时候家里穷,听说红军要买东西吃,刚好村里前几天扛菩萨,家里还有簸箕粄。我提了一香篮粄子上街卖,一会儿就卖完了。又冲回家再提了一篮,也很快卖完了,得了100多个铜片,父亲好开心。我看红军很和善,就说我也要当红军。红军说我太小了,长大了再说。红军给群众发了很多硬纸壳的‘名片’,我当时年纪太小不知道是宣传单,带回家后来被国民党搜走烧掉了。
“1929年底,红军再次从涂坊经过,前往连城新泉。红军前面走,后面就有国民党的中央军部队追来。听驻在涂坊的国民党兵对我说,国军的指挥官和毛泽东是师生关系,后来才没有追击红军,我不知道这事是真是假。我只知道红军第一次来到涂坊,就给穷人撑腰,号召穷人起来闹革命,后来才会有涂坊农民起来暴动。1929年6月19日,张赤男、罗化成领导涂坊暴动。暴动后罗化成在涂家祠宣布成立涂坊乡农民协会,张景威当主席。还成立了赤卫队,由涂凤初当队长。

“1929年10月19日,涂坊举行第二次暴动,成立了涂坊乡苏维埃政府,乡苏设在涂氏满房的老祖屋,涂文政当乡苏主席。后来又成立了涂坊区苏维埃政府,设在涂坊的老路下,现在房子都还在。第二次暴动不到一个月,长汀反动民团黄月波、俞志的武装几百人进入涂坊,到处杀人、烧屋、抢财物。张赤男在宣成接到报信后,派人到上杭蛟洋联系傅柏翠的地方红军,分三路包围涂坊,把造孽的民团赶走了。后来我们吸取教训,扩大了几百人的武装,开展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打仗保卫家乡红色政权。
“可惜后来误杀‘社会民主党’,涂坊很多最早起来革命的骨干都被冤杀,损失太大。涂坊黄竹坑有一对在福州读大学毕业的夫妻,最先被杀,罪名是‘社会民主党’是他们带来的。涂步嵩的儿子涂国琛(时任青年团书记)、涂太英、涂荣珍等人是在涂坊周边山区被杀害的。赖坊的土楼岗有一次杀害了七、八十人,参加红军的团、营、连、排、班各级骨干几乎杀光了。我有个堂哥叫涂华英,是涂坊少先队的书记,因为‘自由恋爱’结了婚,也被杀了,那个场面太可怕太残忍了。后来中央派李明光带部队到涂坊来,才制止了继续‘杀社党’。”
补充团年龄最小的新兵
“1929年底至1930年6月,涂坊是长汀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我年龄小,只能参加儿童团,经常带着一伙同龄孩子在土楼山上出操。县苏军事科的干部看我比较灵活,让我当涂坊乡(后改称红坊)的儿童团队长。队长必须会带操、叫口令,打马刀花、刺枪也要比别人好。我们涂坊革命活动开展早,是‘老苏区’,因为我儿童团队长当得好,所以很快被上级选拔到新区宁化去开展工作。那时候我才12岁。
“开赴新区的工作团有20多个人。在宁化淮土乡,因为反动民团祸害群众,很多偏僻村庄的群众都不敢在家里生活耕作,大量田地都荒掉了。我们工作团的同志开展宣传,动员藏在山上的群众下山回家。挨家挨户上门去询问谁家穷谁家富,划分阶级。帮助当地成立苏维埃政府,选举出乡苏主席等干部,带领贫苦群众分田地。选出乡苏主席后,我们还在淮土住了两夜,过后就回涂坊了。
“1931年,各级苏维埃政府宣传扩大红军,我已经13岁。家里非常穷,我天天闹着当红军,父亲拿我没办法,最后说也好,到部队磨练一下‘更会大’。父亲找到涂坊区苏的裁判部长涂步元,我就这样‘走后门’自愿参加了红军。那一天,我们涂坊参加红军的有50多个人,在乡苏政府集中,沿街上走,没有人送。大家步行经过凹下、三洲往长汀城走,到河龙头住了一夜。第二天继续走到新桥,走了两天才走到新桥往宁化方向十里路的新兵连驻地报到。新兵连设在一座坐西向东有门楼的大屋,连长是一个湖北人,我是连里最小的新兵。
“我们在新兵连天天训练,走队列,开展政治学习,早上要开班务会,交代各种注意事项。平时没有枪,只有站岗的时候有配两支枪。干部特别照顾我,训练一个月,我只轮到一次夜间站岗。连长查哨时故意试探我,我耳朵有点背,但是眼力好,认得他是连长。

我远远地喊‘口令’,连长没有回令,继续走过来。我再喊‘口令’,连长才回令。连长问我如果他是敌人会不会开枪,我说会。他说对,遇上敌人就要开枪,吹紧急哨报警,让大家做好战斗准备。连长对我们很好,处处关心指导我们。因为斗争形势紧张,我们新兵连训练一个月就分配下部队了。
“罗化成当时在福建军区当文化科长,调我去当了7天通信员。后来上级调我到福建军区司令部特务连通信排当兵。到通信排开始有枪背了,我心里可欢喜了。福建军区那时驻扎在长汀的十里铺。我的排长是漳州人,姓张。班长姓吴,是永定人。红军队伍官长士兵自由平等,有个涂坊的新兵本来安排他去担架队,可是他不愿意去。他的哥哥在省苏当土地科长,他想和哥哥离得近一点。姓王的纵队司令心肠很好,看这人一直哭,后来就安排他到军区通信排。我那时候思想简单,只要能留在部队有吃有穿就很开心,现在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幼稚。”
娃娃兵的传令兵生涯
“1934年夏天,国民党中央军的部队十多万人,从龙岩、连城来进攻长汀苏区,红军主力军团在松毛岭组织防御。有一天,上级通知我和几个战友到长汀河田开设通信站。说河田距离松毛岭近,便于传递军事情报和命令信息。说走就走,我们从长汀的东街出发,走路到河田,在河田街上的一间店铺里住下来。站长是永定高梧的吴福清,成员有一个姓赖的江西于都人,一个姓俞的河田人,还有一个永定高梧人,和站长同姓吴。加上我,总共有5个人。
“因为红军缺少军装,我们大多数头上戴着五角星的红军帽子,身上穿的是便衣。背的枪有小马枪、老套筒、俄国造,花式多样。送信时再挎一个干粮袋,里面装有上级的宣传标语口号、部队的秘密口令、军事情报信、前方红军的家信等等。有时两个人同行,任务多时只能一个人单独送信。送信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随传随到随时出发。原先在军区司令部通信排时就去过不少地方。第一次是和一个老兵送信到连城朋口街上的通信站,我跟在老兵身边,一路很平静没有惊吓。从东街送信到童坊,夜里爬大山,黑乎乎的很吓人。山上经常会碰到老虎和毒蛇,有时还会遇上打劫的土匪。后来,从军区驻地送信到长汀宣成区的张屋铺街上,送到宁化安东街上的一间店铺,上级指示到哪里就去哪里。
“我虽然年小,但是脑子灵活,送信去的地方多了,胆子也越来越大。到河田通信站以后,我曾经一个人送信,从河田出发,经过洋坑,翻过松毛岭到上杭古田一条山坑的老屋里。有一次是夜里单独送信到宣成的苏维埃政府。一般传送秘密口令,干部就会交代一定要带上枪。如果不是很重要的物件,就不用带枪。干部和老兵会教我们各种应对突发情况的办法,强调一条:人和枪可以失去,但是情报一定不能丢。在部队我年龄小,大家把我当成子侄老弟,工作生活总是得到体贴照顾,真是托红军的福!
“红军时期部队经常整编,地方武装编入正规军团,四处打仗游击。我从涂坊离家参加红军,向南到过龙岩、上杭、筠门岭,向北到过宁化、清流、归化、武夷山、延平、邵武,还去过长沙。部队的番号也一直在变化,现在都记不起来了。我印象很深的是红军攻打赣州,涂坊有个叫狗头荣的红军回来对我说,打赣州的红军和地方工农赤卫队有好几万人。可是赣州的国民党兵太多了,赣江河宽水深,城墙高大坚固,红军渡河时,对岸白军的伏兵火力太猛,牺牲了很多红军。那个年代,脑壳系在裤头上,生死都是很平常的事。”
万般无奈离开红军队伍
“战争确实很能锻炼人,松毛岭战斗时,我在河田军区通信站工作。先后送军事信到石灰岭、水口等地,还有一次从河田送军事信经过南山坝的老鹰岽到松毛岭。那个时候虽然才16岁,可是我再也不会害怕什么了,老鹰岽很偏僻很阴森,我一个人也没当回事,好像一身是胆一身是劲。在红军队伍里,有团结的战斗集体做依靠;在苏区范围内,有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支持。我觉得能当红军,自己活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离开红军队伍。松毛岭战斗打完后,福建军区的部队和地方武装按照中央的指示节节抵抗。但是敌人实在太多,主力军团都战略转移了,我们地方部队缺枪少弹,硬拼也拼不过,陆续都被敌人打散了。有一天,吴站长写了一封介绍信,发给我们每个人。对我们说目前形势困难,大家暂时分散活动,保存实力。等形势好转了,大家还要在一起工作。我流着眼泪不愿意离开,但是大势所趋,哭也没用。我把站长开的介绍证明藏在身上,从偏僻的深山老林里找路回家。一路上又饿又冷,半走半爬,小小心心往涂坊家乡行走。
“还没到涂坊,就在半路遇到朋口池溪傅发生的民团设卡盘查,每个过路人都要被搜身。当时我只穿了一件单衣,部队的证明信一下就被民团搜出来了,我心想坏事了。没想到有个团丁把证明信撕掉扔进水沟里,抬手打了我两巴掌,就放我过关走了。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到底是民团看我年纪小有意放我的,还是搜身的团丁根本不识字,看不懂介绍信,不然我的命也是保不住的。
“回到家里,看到很多被打散的红军陆续都回家了,有的被关押,有的被罚交‘枪款’,也有的被反动势力杀害。在这个非常时期,红军家属都想尽办法保住亲人的生命。各个姓氏的宗族势力也出面保释红军战俘,慢慢才平静下来。我跟着父亲种地糊口,心里却是盼望红军能早点打回来。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很多失散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重新参加新四军二支队的工作。我因为哥哥参加红军牺牲了,父亲年岁渐大身体多病,家庭需要有人支撑,就此离开了革命队伍。平时种地,闲时到武平岩前一带买卖旧衣物贴补家用。1943年,我年满25岁,和涂坊迳口的刘二莲结婚成家。刘二莲也是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她的前夫是福建团省委书记赖如昌烈士,红军长征后在长汀四都山区打游击时牺牲了。我俩同病相怜,结成夫妻,相依为命。
“现在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什么都买得有、买得起,可是不能忘记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不能忘记涂坊为革命做出的贡献。涂凤初烈士是涂坊的大能人,文化高,书法好,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很有经营头脑。他和罗化成烈士是亲戚,早先在涂坊街上和张世珍的父亲合伙做食盐生意。后来又租用涂义言、涂丁言兄弟的店面开了一间‘同发昌’布店,开了一年多就参加红军工作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涂凤初跟随张鼎丞北上抗日,担任新四军二支队的军需官,在一次战斗中被日本鬼抓住活埋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涂凤初的店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现在拆掉盖新屋了,没有保存下来,很可惜。”
涂龙琛11岁担任儿童团队长,12岁作为外派骨干支援新苏区工作,却直到20岁才开始在涂坊读小学。全国解放后担任过村生产小队长、涂坊乡农会委员,1958年后负责管理公社食堂,参与集体茶山、松脂的生产管理工作。中年开始自学中医,运用祖传秘方为群众服务,至今还坚持为村民看病开药方。他一生吃苦耐劳、谦和友善、性格豁达、乐于助人。采访结束后,老人诚恳地说:“我个人很平凡,没什么值得写的。你们应该多写写那些舍生忘死的革命先辈, 他们才是共产党和红军的优秀代表,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啊!”□摘自《红色文化周刊》
本文作者:红色文化周刊(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