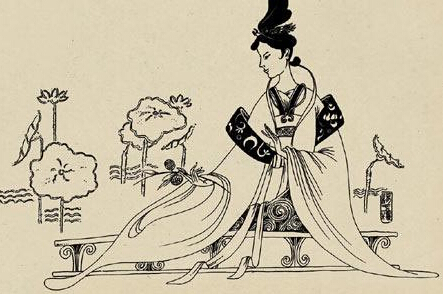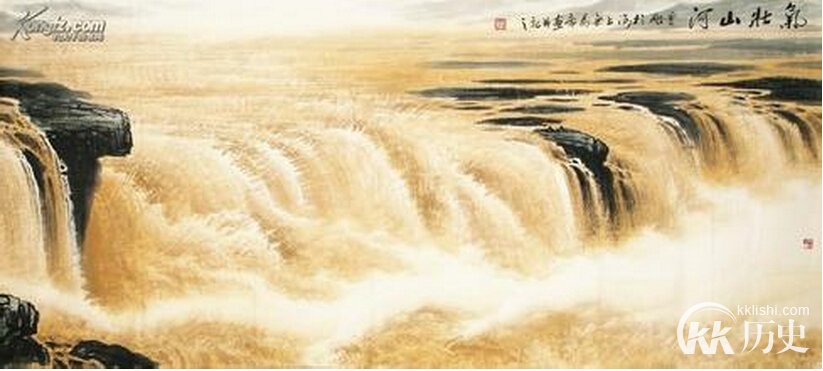拉康 | 亚里士多德的梦野史趣闻

亚里士多德的梦
雅克·拉康 /文
王立秋 /译
译者按
这篇文章是拉康在1978年亚里士多德两千三百年忌辰时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由Lorenzo Chiesa英译,见Lorenzo Chiesa, “Aristotle’s Dream”, in Angelaki, 11:3, 83-84。
人们会区分客体与再现。我们知道,这是为了在思想上再现再现。要说明这点,有这样的词就够了:就像我们说的那样,“引起”或“唤起”再现。
亚里士多德是如何构想再现的呢?我们只能借助他的时代的一些弟子留下的东西来认识这点。弟子重复大师说的话。但条件是,大师知道他在说什么。除弟子外,谁又能对此作出判断呢?因此,知道的,是弟子。不幸的是——这里我必须像一个精神分析家一样见证——他们也做梦。
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做梦。感到有义务解释亚历山大围攻推罗(Tyrus)的梦的是他么?萨提罗斯(Satyros)——推罗是你的。一个典型的阐释-游戏。
三段论——亚里士多德实践的三段论——是梦里出来的么?必须说,三段论是永远站不住脚的;原则上它有三部分,但实际上它只是普遍对特殊的应用。“所有人都是要死的”,所以他们中的一个人也必然会死。弗洛伊德领会到了这点,他说,人欲望它。
证明它的是梦。没有什么比梦到我们被谴罚去重复地生活更可怕了。死亡驱力的观念便来源于此。脑子里想着死亡驱力的弗洛伊德式的亚里士多德派认为,亚里士多德接合了普遍与特殊,也就是说,他们把他变成某种类似于精神分析家的存在。
不时地,被心理分析的人也会用三段论,也就是说,他会亚里士多德化。亚里士多德持续做主。这不是说他活着;他在他的梦中幸存。在每一个被心理分析的人身上,都有一个亚里士多德的弟子。但必须说,普遍的,不时地也会在闲谈中自我实现。
肯定了,闲谈的是人。他带着相当的自满闲谈。这点,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表明:即,被精神分析的人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回到精神分析家那里去。他相信普遍,为什么并不清楚,因为他是作为一个特殊的个体放弃自己,把自己交给所谓精神分析家来照料的。
就被精神分析的人梦到精神分析家干涉而言。问题是唤醒被精神分析的人么?但他在任何环境下都是不想被唤醒的;他做梦,也就是说,他坚持其症候的特殊性。
《论灵魂》(Peri psuches)一点儿也不怀疑真理的存在,这就构成了对精神分析的抵抗。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与亚里士多德有龃龉,后者,在此灵魂之生意上,并没有说过什么好话——如果书写保存下来的,是忠信的言说的话。
“to ti esti”和“to tie n einai”,我们翻译成“本质”与“实质”之间的区分,就其乃是有限的(“to horismon”)而言,反映了实在中的一种区分,即言辞和受言辞影响的实在之间的区分。这也就是我所区分的象征与真实。
诚然,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不存在性关系,也就是说,在人类那里,不存在女性的普遍,不存在“全体女人”,随之而来的是,在精神分析家和被精神分析的人之间总是存在额外的某人。存在这样的东西,我不会把它定义为再现,而要把它定义为对象的呈现。这种对象的呈现就是我有时说的对象a。这玩意儿极端复杂。
亚里士多德忽视了这个因为他相信存在再现,而这就引出了弗洛伊德写的那些东西。亚里士多德认为——他没有这样总结但他就是这样——他思想世界,而与此同时他就像我们所说的全世界,也就是说,人一样做梦。他和所有那些说话的人一样,梦想着他思想的世界。结果——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思想的,是世界。第一天球就是他所说的“努斯”。
我们不可能知道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家总谵语。当然,弗洛伊德也谵语。他谵语,但他指出他说到了(多个)数字和表面。亚里士多德可能会设想拓扑学的存在,但这方面无迹可寻。
我已经谈论过醒。情况是,我最近也梦到闹钟响。弗洛伊德说在我们不想醒的时候我们会梦到醒。
不时地,被精神分析的人也会引用亚里士多德。那是他的材料的一部分。因此,在精神分析家和被精神分析的人之间总有四个人格。不时地,被精神分析的人也会生产亚里士多德。但精神分析家背后还有他的无意识,不时地,为给出某种阐释,他本人也会利用这个无意识。
这就是我能说的一切了。我在梦里产生闹钟响的幻觉这个事实,我认为是个好的迹象,因为,和弗洛伊德说的不一样,情况是,我醒了。这是在这个情况下,我醒了。



拜德雅(Paideia):思的虔诚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品○●○●
“导读”系列衍生的一个图书品牌
拜德雅

长按左侧二维码关注
本文作者:拜德雅(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