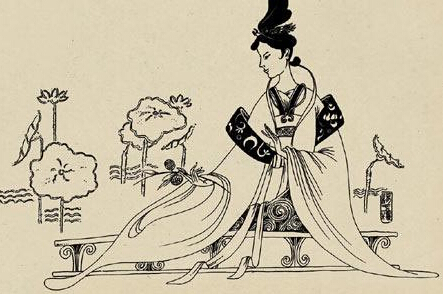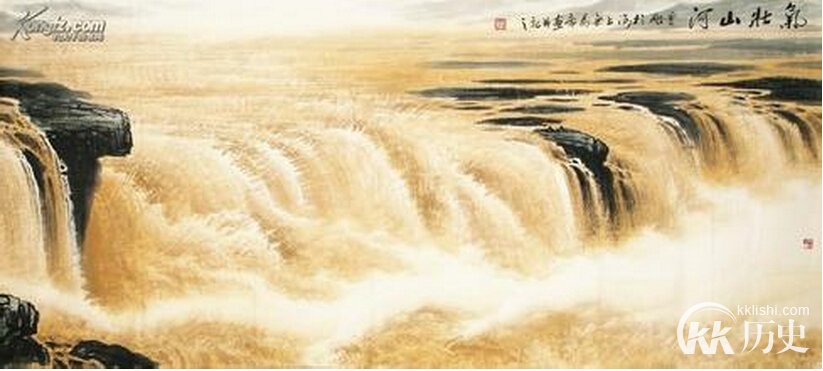宋子文初恋盛七小姐 | 当时只道是寻常野史趣闻

●
1900年,盛氏家族是上海滩第一豪门。
淮海中路的盛公馆富丽堂皇。宅前花园,遍生琪花瑶草。草坪三亩,置古船木秋千椅,砌汉白玉喷水池。高墙内外,迥然天壤。拾级而上,门厅廊柱支撑内藏式阳台,琉璃天棚镂下楚楚动人的斑驳日光。穿过门厅,即是四层主宅。首层客堂餐厅,卧室浴室分布其上。大理石穹窿,柚木地板,彩绘壁画,紫铜门窗拉手,空铸梅花窗栏。
中西合璧,美轮美奂,可堪白玉为堂金作马。
彼年盛夏,公馆传出喜讯,盛七小姐出世。
我就是盛七小姐。

父亲盛宣怀志在匡时,胆魄卓尔,为李鸿章之股肱,办洋务实业。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母亲庄氏,出身常州望族,世代书香,簪缨传家。我含匙而生,是盛家掌上明珠,富贵自不是寻常人家女孩可比,规矩却也极严。
1911年辛亥革命,革了清廷之命,也革力保大清的臣子之命。父亲转瞬成千夫所指,流亡日本。盛家四面楚歌,母亲运筹帷幄,终得保全。五年后,父亲去世,出殡仪式是一场胜似国葬的盛典。尽管如此,末世预感仍浓云不散,危如累卵。
盛家已不是从前的盛家了。
不过是旧时王谢。
山雨欲来风满楼。
每日晨起,我独坐草坪秋千读诗,总遥遥望见一位年轻人登门,西装革履,气度不俗,听说是四哥的秘书。四哥纨绔天性,夜夜流连灯红酒绿,白天日上三竿也不起身。秘书汇报工作却一向准时,似是克己之人。
多数时候,他在客堂独自等候,读报喝茶。母亲偶尔会来客堂和他说话。日子久了,我对他也有所了解。他叫宋子文,留洋归来,学识广博。盛家虽不似旧时荣耀,但能登得起盛家高门的,也非庸碌之辈。
“宋先生,听闻您留洋海外,想必英文定是出色,不知可否做我的英文老师?”时代骤变,普天之下崇洋之风盛行。我虽是女子,却不愿拘于琴棋书画绣的女儿工夫,多些技艺傍身总是有益。
宋子文欣然答应,每天等候四哥的时辰,用来教我英语。
朝夕相对,我深感他志向凌云,非池中物。

“其实我很早就留意到七小姐,清晨总在草坪秋千上读书。不知读的是什么书?”
“是些诗词。我偏爱古文古诗,沉淀了千百年的情意,有种时光的沉香。”
“难怪七小姐气质古典。”
“整日学洋文,总觉得洋文表情达意,未免太过直接露骨,少了含蓄朦胧处。”
“宋某年少留洋,读诗不多,最钟爱苏东坡的《蝶恋花·春景》: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我抬眼看他,他双眸间,尽是相思意。
“公子多情,怕要早生华发了。”
眼波流转处,云烟四起,顾盼倾城。

“这些天,你和宋先生走得挺近。”母亲斜倚在黄花梨贵妃榻上,看似漫不经心地问我。
“宋秘书来汇报工作,四哥总不起床。宋先生候着,顺便教我英文罢了。”
“学点洋文,见多识广,倒是好的。我身子一日不如一日,将来打点家业,还是得落在老四和你身上。”
“您还年轻,别说这些。”
“不年轻了,但还算耳聪目明。近来常听闻有关你和宋先生的闲言碎语,”母亲微微扬眉,“盛家的小姐,可不要妄自轻薄了身份。”语气沉肃,不怒自威。
此后,我托辞不再向他学英语。盛家规矩严苛,父亲离世后,母亲精于治家,素来说一不二。我与他虽互生情愫,却是母命难违。
剪不断,理还乱。
我照例读诗,日复一日。

“七小姐,不知宋某是否有得罪之处,换来你连日淡漠以对。”子文未进客堂,径直走向秋千上的我。
我把诗书放在一旁,起身,浅笑,“宋先生依旧早到。”
“我心依然,只怕小姐的秋千,已不似从前了。”
“先生是在怨我吗?”
“七小姐,我对你一往情深,你怎会不知。那么,我在你心里是何位置呢?多情却被无情恼,如今看来,宋某心意不过是一番庸人自扰。”
“宋先生喜欢这首词,该不会忘了这词里还有一句:天涯何处无芳草。”心底凄凄,杂陈汹涌,面上却佯作波澜不惊。
“你对我从未动过情吗?”子文注视着我,悲凉盈千。
“宋先生,庭院深深深几许。生在豪门,多的是情非得已。”我撇下他,回屋了。

母亲在客堂,正襟危坐。见我进屋,便牵我同回卧房,闭了门说话。
“我私下命人打听了宋先生的家世底细。”母亲说道。
“年纪轻轻,海外留学,家境应当不差。”
“此言差矣。宋先生家在广东,父亲是教堂里拉琴的。我们盛家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名门,门不当户不对,你们二人趁早结束。免得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母亲态度决绝,不留余地。
“宋先生是能成大器之人。”
“看来,你对他当真是有意了。”母亲深深地望着我。
我走到母亲身边,握着她的手,动情地讲,“姆妈,我生在盛家,正当妙龄,富家子弟追求者众,无人可使我动心。宋先生志存高远,有闯劲,肯拼搏,没有那些公子哥生就的傲慢和懒散,待我也真心。给彼此一个机会,总好过以门第之辞拒绝。”
“我明白,能入你眼的人太少,也欣赏宋先生的兢兢业业。可是,你可知他姐姐宋庆龄嫁了孙中山?”
我满眼疑惑。
“若无辛亥年间,孙中山带领的那场革命,你父亲怎至于流落日本,盛家何以式微若此。自古以来,君臣之道,你父亲是人臣,殚精竭虑誓保大清,所谓各为其主,本是尽了忠君本分。然而,历史从来都是成王败寇。倘大清尚在,孙中山等不过是乱臣贼子。大清既亡,革命党便将前朝位高权重之人置于死地。当年你还小,你父亲在日本,我携全家逃亡,家门上偷偷挂了洋行牌子,托洋人朋友暂住,这才保全盛公馆,未被没收洗劫。这些年来的世态炎凉、惊涛骇浪,我从未道与外人,却仍是不想,你与仇家共处一室啊!”母亲说着,竟泪眼朦胧。
母亲一生坚毅果决,我还没见过她落泪。父亲辞世,母亲一介女流,力挽狂澜,在乱世的上海滩,撑起了整个家族。个中苦楚,远非等闲女子承受得起。
“这些心事切勿对外人言,毕竟清廷已逝,不要徒惹是非。对宋先生,只说门第不当便是。”母亲不忘叮嘱我。
在母亲有生之年,我和宋子文,断断不能相恋了。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

“停车!”
四哥载我出门,半路被人拦下。也怪四哥张扬,给自己的豪车上了“4444”的牌照,所过之处,人尽皆知,盛老四到了。
“是谁撒野?”四哥问司机。
“拦车的是宋秘书。”
四哥看我一眼,意味深长。
“宋先生说,要和盛七小姐对话。”司机说。
“见不见?”四哥问我。
“何必再见。”我满目萧然,声音寂寂。
“走吧,绕开宋先生。”四哥指挥。

“宋先生执意要见小姐,不肯让道。车外已有多人围观,久了怕有闲话。”司机为难地说。
我下了车,站在门口。
他向我走来,目光如炬。
“七小姐,我不会放弃的。努力过而无结果和不努力就认输,我更不能接受后者。”
字字深沉,刻骨如也。
“说完了吗?说完我要走了。”
车门关上的一霎,泪如雨下。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情深无益。

晚饭时,四哥说,已将宋子文调到武汉任职。
这段孽缘,也该断了。
终究是懵懂年华里,一场倾尽心力的初恋思慕,怎能不让我牵心挂肚。我终日郁郁寡欢,饭茶不思。八妹见我日益憔悴,相约同去钱塘江观潮。
杭州桂花正盛,香甜怡人,满城的浓情蜜意。听人说,桂花寓意“永伴佳人”,只恐花愿好,人成各。
心灰意懒之时,看花满眼泪,徒添伤悲。

“七小姐,你好吗?”
钱塘江涛声呜咽,我隐约听到子文的声音。许是思念太用力,生了幻听。
忽然有人拥住我的肩。
我一惊,猛地回头,竟是宋子文。
面前站着的,是我朝思暮想,以为永世诀别不见的人。行到山穷水尽处,忽见得柳暗花明,眼泪瞬间盈眶。又怕泪蒙了眼,看不清所爱之人容颜,不敢任眼泪打转。到最后,多少爱意澎湃汹涌,悉数化作眼底一抹不胜凉风的娇羞,只是轻声说,“你来了。”
我信他懂我的九曲心思。既是我良人,必知我情深。
他只是拥抱我,在我耳畔讲,“对,我来了。”

远离盛公馆,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用最虔诚的容颜,祈祷一场纯粹的爱恋,与名利地位无关。
观潮,赏桂,望月。那几日,是我生命里最陶然的时光。
当时只道是寻常。
离杭赴沪那天,子文拿出三张船票。
“经姐姐引荐,我被孙中山任用,邀我赴粤。我要带你和八妹一起走。革命必将成功,我们一同去闯天下吧!”
我喜欢他志在必得的桀骜。时势造英雄。他志在千里,定会建功立业,有所作为。
可是,思及父亲的亡故、母亲的泪水、盛家的叹息,实在无法与之共赴广州,与孙中山相见。盛氏庞然,却仅我与四哥是母亲所生,其余兄弟姐妹都是姨娘们的孩子,必不会对母亲尽孝。母亲辛苦一世,我怎忍见她晚景凄凉,无人顾念。
思前想后,我眼下须为母亲养老送终,不能随之南下。母亲在世,我便尽心伺候,不思嫁娶。母亲寿终正寝,我再嫁宋,也算未曾忤逆母上心意,可得两全。
我赠一柄金叶子给他,“我如今尚不可与你同去广州,赠君此叶以定情。古人说‘君心如磐石,妾心如蒲草。蒲草韧如丝,磐石无转移’,我在淮海中路盛公馆的秋千架,等你回来。”
他黯然神伤,“纵使秋千依旧,怕红颜不似。”
“我七小姐既说了要等你,就一定会等。”
翌日,他起程去了广州,我们回上海。
我知道,这不是告别,而是开始。
茫茫碧落,天上人间情一诺。

二十七岁那年,母亲病逝。
盛氏家族忽喇喇似大厦倾。盛公馆雕栏玉砌犹在,只是朱颜改。至亲离世,身旁无人陪伴倾诉,痛苦愈加深重。
正当我心力交瘁时,四哥却坏了规矩。
四哥打算将遗产分与盛家几位公子和侄儿,把待字闺中的我和八妹排除在外。家族中,只有我与四哥系庄夫人亲生,一母同胞,相煎何太急!
我熟悉法条,依据民国男女平等的相关法律,未嫁女子享有与胞兄弟同等的财产继承权,四哥无权剥夺。
亲生兄妹,对簿公堂,何其凄凉。
最终,我赢了官司,分得白银五十万两。八妹亦如是。
过往浮华,宛若南柯。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盛家,已成倾巢。

山河依旧在,不见故人来。
上门提亲的人不少,我只是望眼欲穿地盼子文归来。
盼到的只有一则新闻:
1927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与九江富商张谋如之女张乐怡喜结连理。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早年,我痛下决心,挥断情丝,屡屡拒绝,是你几度挽回,山盟海誓,我才终下决心,与子偕老。谁承想,说过非我不娶的人,一转身就牵了别人的手,许了她共白头。
昔日情分,信誓旦旦,皆是有口无心吗?
蒲草依旧韧如丝,磐石已斗转星移。
人面不知何处去。

我大病一场。五年后,潦草嫁人。
爱是一场费心费力的徒劳,燃尽初心,心字已成灰。既已成灰,又过了而立,徐娘半老,只求平淡度日。
一日午后,五哥来电,邀我喝茶。
走进五哥家客厅,沙发上坐着五哥,五嫂,和宋子文。
我转身欲走。
五哥忙说,“七妹,好久不来,怎么刚见面就急着走呢?”
我停下脚步,心想总不好拂了五哥的面子。再怎样不愿久留,也还是坐下喝杯茶再走。

“七小姐依然明艳动人。”宋子文凝视我说。
“宋太太怎么没一同来?”我冷口冷面,眼里尽是寒霜。心里天寒地冻,面上怎会桃之夭夭。
他登时错愕无言,很是尴尬。
我已不是当年心思透明的少女,眉眼间都是切切温情。此去经年,丧母之痛,兄长欺凌,恋人背叛,家族衰微。岁月的风雪把我磨得刻薄寡淡,无情则无伤情。
五哥解围,“当年大家年少无知,想来彼此有些不悦。不过时隔已久,对儿时纠葛,也该释怀了。宋先生此行,专程看望七妹,我和你嫂子不便打扰,你们叙叙旧吧。”五哥五嫂起身,回里屋去了。
既然哥哥不在,我也无需顾及谁人颜面。
“宋先生好生坐着,我先回去了。”
“七小姐,一起吃晚饭吧。”
“不行,我丈夫还在家等着我。”说完,我拂袖而去。
如今,他高官厚禄,春风得意,再不是当年日日登门汇报工作的文弱书生。五哥敬他是人中龙凤,可我不屑攀附。
在我心里,他只是一个负心人。
夜来幽梦,常回那年江畔,高傲而坚定:“我七小姐既说了要等你,就一定会等。”
可你,不值得我等。

我原想,此生与宋子文永无羁缠,谁知天意弄人,命运又将我们转作一处。
早年搬离盛公馆,令人在新居亦建一架秋千。
我喜欢秋千的自由。不似人生,有太多业障牵绊。
秋千院落落花寒。
陪儿女在秋千上玩耍,四哥来了。
当年为了钱财,法庭相见,心无芥蒂是不可能的。
“七妹,四哥是来求你帮忙的。”几年不见,四哥白发苍苍,颇显老态,再无当年风流倜傥的少爷模样。我心里恍然漾出几许不忍。
“进屋说吧。”我让保姆看着孩子,带他进了屋。
“犬子被关了监狱,我和你嫂子急得团团转。能动的脑筋都动了,能托的关系都托遍,可就是不见放人。”
“犯了大错吗?”
“小错而已。时局动荡,抓人放人全凭权势者一句话。”四哥哀叹。
“我能帮你什么呢?”
“宋子文如今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位高权重,如日中天,和妹妹有旧。七妹如能给宋院长打个电话,事情就好办了。”
我心伤未愈,又听四哥相求,骤然愠怒。
“四哥不是不知,我与宋子文已一刀两断。当日在五哥家,如何不留情面,话已说绝,想必你也听说了。现在我再去求他,岂非轻贱自己?盛家的人,颜面荣辱是何等重要!”
四哥颓唐沮丧,黯然走了。

两日后,一个年轻女孩来访,说是四哥儿媳。这些年不相往来,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竟是未曾见过。
她跪倒在地。
“七姑母,如今只有你能救我丈夫,你若不帮我,我就长跪不起。”她梨花带雨,楚楚可怜。
我无计可施,只得答应。这两日,心下反反复复。毕竟是亲侄,不忍见死不救。
只是当初对宋子文不屑一顾,今日却要乞哀告怜。
世事无常。
“电话只打一次,成就成,不成,不许再来请求。”我冷若冰霜。
拨电话的时候,我双手冰凉。这么多年,他仍是我心里一根断刺。一触便痛,痛断肝肠。

没想到宋子文一口答应。
我担心空口无凭,夜长梦多,又说,“我想明天中午跟我侄子吃饭。”
“七小姐开口,没有宋某办不成的事。”
次日中午,四哥的儿子果然获释。

四哥感念我不计前嫌,出手相助,设宴款待全家。分崩离析的盛家今又重聚,琉璃光盏,觥筹交错,依稀可见往日气派。只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我想,宋子文是念我的,不然也不会轻易应允我的请求。
倘若我敢跟他走,又或他情愿守诺,必不是劳燕分飞的戚戚。说到底,我们都更爱自己,却高估了对方的情义。以为此时此刻的偏爱即是永恒,仗着零零星星的垂怜,便有恃无恐。他是政客,我不知他娶富商之女,是出于爱,还是其他考虑。我只知道,在他心里,盛七小姐永远有一席之地。
断肠声里忆平生。
我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文字已获作者授权,图片摘自网络,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旧事集
❤
夏日的《徒然草》
本文作者:小镇的诗(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