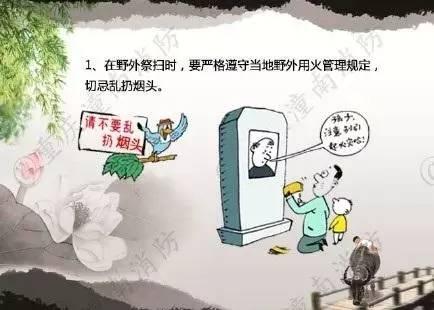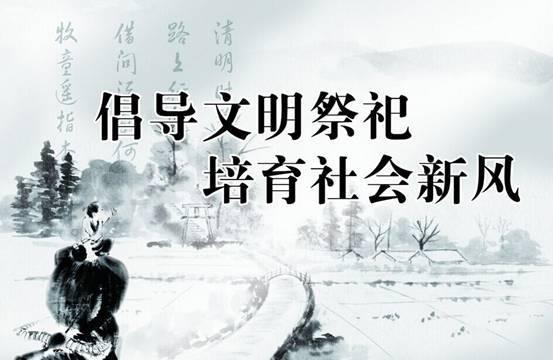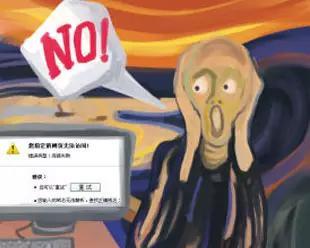南澳海岛的祭祀文化野史趣闻

南澳位于台湾海峡喇叭口的西南端,每年属于8级以上强风日数平均达88天,也因此而有“风县”之称
岛上中间是高山,周围是平地,有海港,有庙宇,有村庄。
为避风沙之害,村庄多建在避风之处。
南澳人特别关注天气变化,气象意识极强。
过去,讨海人逢见面三句不离天气预报。
家家户户必有一台收音机,每天固定看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在很多人心里新闻联播只是陪跑,七点三十的气象播报才是正牌。

这是大陆城镇少有的。
如遇气象预警,各家各户迅速行动,渔船回港避风港和对住宅加固防风是必做的两件大事。
这种临机应变意识来源于南澳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南澳人的信仰。
南澳之名,始于隋朝。
南即南方,澳指可泊船之处。
只计南澳主岛,就有30来个含有“澳”字的地名。
有的是镇,如深澳、隆澳(今称后宅)、云澳。
有的是村,如澳前、青澳、东澳、三澳。
可见南澳是实打实的悬海孤岛。

90年代的南澳岛,公路上没有车水马龙,渔村安安静静。
平日里会有以农耕为主的本地菜农吆街卖菜,现在还留有卖草街路;偶
有从大陆来的手艺人走街串巷磨剪子戗菜刀;

或是白糖客挑着白糖边走边拿小铁锤敲着小铁片挨家挨户吆喝以旧物换糖咯。
这些声音就像湖泊中荡漾的涟漪,映衬得渔村里更加安静。
南澳人住家毕生追求独门独院,但邻里关系非常亲热。
平日里,谁家讨海归来都会慷慨热情地把渔获馈赠邻舍。
谁家做饭缺个萝卜少根蒜都会找隔壁要,非常方便。
时来节到,谁家吃香饭做蚵仔煎一定会装一大碗和厝边头尾分享。

特殊时期,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邻里除了出人出力,还会给份子钱,和城市邻居相比多的不是一星半点的义气。
这种邻里相帮相扶深度契合海岛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特点。
从这个角度讲,南澳的祭祀文化是一种功利的文化。
住在海岛上的居民诸神崇拜,拜祖先,拜鬼神。
平日里省吃俭用,一到年节祭拜出手豪气。
大到献戏、捐香油钱;小到杀鸡宰鹅买生果摆供桌,采买灯油香烛、元宝金银和炮仗。
总之,三牲四果五齐等多种祭祀供品种类繁多到让人眼花缭乱。
据不完全统计,生活在海岛上的主妇的月行程是这样的:

初一、十五拜天公,
初二、十六拜厝祖,
初七、二十一拜三山国王,
初九、二十三拜观音,
初十、二十四拜佛祖。
另外,每日例行一炷香拜家里的神。
祭拜时间之频繁令人瞠目结舌,祭祀对象之复杂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尤其是正月,从年三十到正月十五,几乎一天一小拜,两天一大拜。
当然,没有坐过红头船在大海上乘风破浪的人是很难理解南澳主妇这种虔诚与敬畏的。
这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的崇拜。
向晴雨无常的大海讨生活,堪比蚍蜉撼大树,除了勤劳勇敢,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剩下的能也就只能听天由命。
南澳的红头船,一说是缘起于雍正元年,那时规定广东商船船头及大桅上部漆红色,所以才叫红头船。
一说是潮汕地区迷信,认为红色的船头能够趋吉避凶。
有一年春节,云澳一渔村上有一艘红头船,因为点守岁烛,整船付之一炬。
大家都很痛惜,一艘木红头船造价50多万,这一对守岁烛烧去的不止是一艘船,顺带把这一户渔民烧成倾家荡产。
船老大大悲大痛之余却说:“风吹鸡蛋壳,财去人安乐”。
“财去人安乐!”这话乍看就是一句自我安慰,但其实非常有智慧。
如果钱财散去就可以免去灾难,那也未尝不可。

只要创造财富的人健在,就可以再重新积蓄力量,蓄势待发。
钱财固然重要,但身体更重要。
南澳的讨海人既有大海一样的胸襟,有乘风破浪的胆魄,又有安生认命、小进则满的安乐观。
他们一方面勇于拿命和大海搏杀,一方面小富则安。
在海上提心吊胆、辛苦危险的讨生活,上岸回家,有鱼吃,就非常不错。
有肉吃,就知足了。
有酒喝,那还有什么好追求的。
洋楼盖起来,这一生也就够了。
我曾经在祭拜的时候竖起耳朵细细听主妇们的祷告,说来说去,不过就那么几句:四季平安,家庭和睦,添丁发财!
尽管心愿很单纯,但是祭祀花费往往令人瞠目结舌。
自秦汉中原人迁入潮汕地区至今,南澳人的祭祀习俗自具特色,既有自古传承的,又有因海岛地理环境而变异生成的。
时至今日,南澳的祭祀礼仪和习俗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衰败和没落。

那些顺应祭祀习俗而生的传统老手工艺不仅没有大发展,反之流于机械化生产,个性与人情味消失殆尽。
大街上再也见不到愿意虔诚地端坐在木墩前认真细致地錾纸的手艺人,印刷机印刷的现代纸钱也在日渐取代手艺人手打的传统纸钱。
敬奉神明的很多供品也不再由主妇诚心亲手烹制准备,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化生产的成品。
老一辈人珍而重之的很多祭祀礼仪在新一代主妇手上慢慢被遗忘……
祭祀是为了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对祖先的缅怀,祈求降福免灾。
本文作者:南澳故事(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