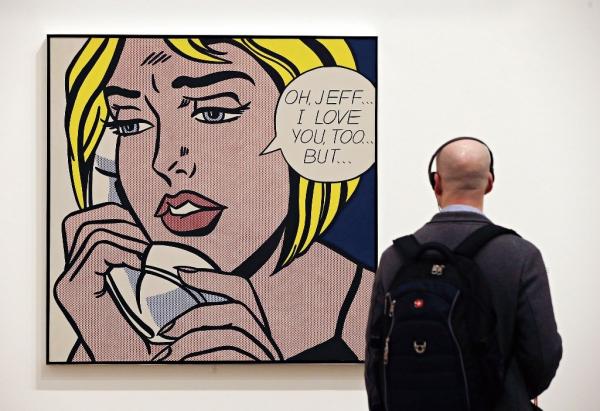卡达莱的小说世界:以古老传说抵抗国家现状历史文化

阿尔巴尼亚,这个今天很多年轻人几乎没听说过的国家,在我们小时候却是“欧洲的一盏明灯”。它不大,只有两百多万人口,从地图上看像是一只耳朵,但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却巍然耸立,响当当一条好汉,我们最亲最亲的兄弟。
但到了1970年代中期,那种亲如兄弟的感觉却不知不觉淡去了,直到有一天,两个国家公然闹翻。随后,中国进入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突然精彩起来,有比《地下游击队》更好看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有比“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更好听的“啊,朋友,再见”,更有“封闭的贫乏”不可比拟的“开放的丰饶”。我们有太多的向往,太多的忧虑,那个叫阿尔巴尼亚的国家还有消息吗?不知道,没注意!
卡达莱1936年生于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山城吉罗卡斯特,童年时代经历了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占领。二战结束后,他先在地拉那大学历史系读书,后赴莫斯科留学。他18岁开始写诗,27岁发表长诗《群山为何沉思》,接到总理霍查的电话,奠定了他在阿国首席诗人的地位。2005年获得首届英国布克国际文学奖。近来年,卡达莱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很高。
阿国出了个卡达莱
但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中国读者一直甚少读到阿尔巴尼亚文学,后来再也看不见这个国家,似乎也顺理成章了。
但突然,“阿尔巴尼亚出了个卡达莱”,消息不胫而走。出版界行动起来了,先是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破碎的四月》(孙淑慧译)、《亡军的将领》(郑恩波译)、《梦幻宫殿》(高兴译),花城出版社又在2012年初一下子推出了卡达莱的《石头城纪事》(李玉民译)、《错宴》(余中先译)和《谁带回了杜伦迪娜》(邹琰译)。
谁是卡达莱?其实中国读者应该与他最早相遇。阿国选择反修路线时,正是卡达莱创作的成名期。1963年,他就出版了蜚声欧洲的长篇小说《将军的亡灵》。作为阿国亲如兄弟的盟友,中国曾热烈地介绍过他,只是我们的介绍侧重于他的政治抒情诗。也就是说,在卡达莱名声如日中天时,作家的两个身份——发掘民族历史的小说家和诗人,只被汉语择其一。
卡达莱出生于1936年,18岁出版诗集,27岁发表长诗《群山为何沉思》(1963),接到总理霍查的电话,也奠定了他在阿国首席诗人的地位。此后,又以同样轰动的方式发表了长诗《山鹰在高高飞翔》(1966)、《六十年代》(1969),并成为劳动党中央委员。《山鹰》开首便写:“秋天的夜晚来了,/共产党员们向四处分散;/平原进入梦乡,/躺在山脚下边……”(郑恩波译)。中国读者若在贺敬之、郭小川的延长线上阅读卡达莱,应该大体不错。
但卡达莱的小说却是另一番模样。他的小说,几乎每一部都带给人们一个奇异的世界,我们根本无法在柳青、杨沫、梁斌或《卓娅与舒拉》的延长线上阅读,也无法报之以中国读者惯常的东欧作家想象。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虽因创作而遭遇过内部调查,但看起来并没有受到政治迫害,以致1991年后,他也因官方作家身份受到冲击。随后移居法国,先后出版了《金字塔》(1992)、《四月冷花》(2000)、《阿伽门农的女儿》(2003,旧作)、《事故》(2008)和《错宴》(2009)等,成为蜚声世界的大作家。
小说与政治
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犹如一颗原子弹在国际共运内部炸响。随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向,跟随苏联告别斯大林时代。中阿两国则义无反顾地坚持把斯大林当做革命导师,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反修”道路。两个国家迅速亲近起来,成就了一段传奇般的友谊。
在中国进行“文革”时,阿尔巴尼亚也开展了“思想文化革命”。尽管我们对此所知甚少,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阿国作家绝没有苏联和东欧因顾忌西方舆论而留给作家们的那一小点宽松。阿尔巴尼亚的残酷政治清洗,直到中国走入改革开放之后还在持续进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能理解卡达莱何以写出了真诚的颂歌,但又诧异他何以能出版内涵深邃的小说。
既然从那个严酷的政治时代走来,那么中国读者也像西方读者一样,关心卡达莱小说的政治性。但与西方读者仅关注文学的直接对抗性不同,中国读者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探寻贫乏与丰满、字面和隐喻、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张力,以及从这种张力中挤出来的“政治性”;也会借此探寻阿国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实施规范的边界。
以《谁带回了杜伦迪娜》为例:
在拜占庭和罗马教廷争夺公国的时代,弗拉纳也家的九个儿子在同一个季节相继死去,家里惟一的女儿此前刚被远嫁中欧。一夕之间,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家族只剩下一位老太太。可三年后的一个夜晚,远嫁的女儿突然被三哥康斯坦丁带回家中。老太太惊讶不已,因为康斯坦丁早在三年前就已葬入墓地;杜伦迪娜更是惊恐万分:在15天的路程中,坐在她前面的那个骑马人竟然是个幽灵!消息迅速传开,地方治安官也立即赶到现场……
该书出版于1980年,正是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决裂,选择了彻底与世隔绝的时刻。于是,西方批评家从中读出了卡达莱以古老传说抵抗国家现状的含义:杜伦迪娜远嫁他乡,康斯坦丁“从墓中站起来”,开始漫长的穿越欧洲之旅,皆“来自和世纪交流的愿望”(法文版编者序)。
在一个有着类似历史经验的中国读者看来,这部小说的政治性当然不会是政治对抗,也不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而是蕴含在“迷信”(幽灵)与“理性”的对立中。而卡达莱站在了“迷信”一边,也就站在了劳动党中央一边,因为代表“理性”的恰恰是拜占庭,那个和罗马教廷都在觊觎阿尔巴尼亚的国际集团。
而小说的“迷信”,正是以古老的传说形式出现的。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劳动党人并不排斥民间传说,相反,很多时候倒是乐于从中发掘爱国主义资源。无疑,从坟墓中站起来的康斯坦丁,穿越漫长的旅程把远嫁的妹妹带回来,正是这种资源之一。而这种神秘的传说,则让肩负帝国使命的大主教感到紧张:
“从坟墓里出来……”斯特斯重复,“一个愚蠢的谣传!”
“这没那么简单,”大主教打断他,“这是个可怕的异端邪说。极端的异端邪说。……今天,只有耶稣基督从坟墓里出来,你理解我的意思吗,上尉?”
从这时开始,一直以理性态度调查此事的当地治安官斯特斯上尉,开始偏离了“理性”,走向了“迷信”,因为“理性”被权力玷污了。
表面上看来,治安官的调查与大主教的要求是一致的,都是基于“理性”,不相信神秘的复活事件发生。但大主教命令他拿出确凿的证据:“要坚持不懈,到处去找,直到找到那个人。”然后话锋一转:“要是找不到,就要创造一个出来!”追求理性(真理)到了丧失理性、欺世蒙人的地步,那么,迷信的古老传说便挣脱出规定的爱国主义轨道,显现出它动人的穿透力。
小说的结局符合大主教的指令方向,也符合“理性”的原则:那个带回杜伦迪娜的人,终于在国境线附近被捉拿归案,治安官亲自审理,案犯如实交代。审理报告递交上去后,亲王和主教安排了一个“破除迷信”的两千人大会,由治安官宣读调查结果。远近的乡民和贵族,遥远的拜占庭的代表,纷至沓来。
但就在官方安排顺利进行、渐趋高潮之际,治安官却出人意料地宣布:带回杜伦迪娜的人就是走出坟墓的康斯坦丁,那个被捉拿归案的流浪汉是被人收买的。而他,相信康斯坦丁的复活,相信康斯坦丁留下的“承诺”。治安官也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朴素风格与艺术迷宫
中阿两国在历史上都曾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惟一道路。其间的困厄很多,之一便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往往被定为惟一的方法。但在中国靠一场“先锋文学”运动才彻底引入并合法化的“艺术迷宫”式的表现手段,在卡达莱那里却先天就存在着,而且那么朴素,那么引人入胜,不似中国许多先锋文学,充斥着人为痕迹和无病呻吟的矫情。这也为卡达莱广泛展示阿国历史画卷和民族心灵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梦幻宫殿》是卡达莱为数不多的遭禁作品之一:
在奥斯曼帝国首都一个显赫的阿尔巴尼亚家族中,历代都有人充任苏丹的重臣,但也常遭受流血清洗的重创。这一切都跟梦幻宫殿有关。这是帝国的一个重要机构,负责搜集每个臣民的梦,甄别、筛选、分类、评级,从中分析帝国的安危。一只蝴蝶也能扇动起千里外的风暴,库普利里家族便安排他们的外甥入梦幻宫殿就职。于是,懵懵懂懂的马克-阿莱姆犹如K走向城堡,也如K走进诉讼程序,开始了充满诡异、神秘、恐惧、疏离的梦幻宫殿经历;宫殿里既无生气,也无人格,完全笼罩在卡夫卡笔下的氛围里……
如果依照中国读者的东欧作家想象模式,而不考虑阿国的政治现实和卡达莱的歌手身份,一定会认为这也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即使有着设身处地的考虑,我们仍然不明白卡达莱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和遭禁后何以作家本人却无碍的奥秘。小说本身写的就是一个迷宫,长长的空旷无人的走廊,没有任何标志的房间,无人格的面孔和极为克制的言谈,操纵世人生杀大权的神秘存在,和令人惊讶不已的荒谬事物,被作者自然而巧妙地组合进一个动人心魄的艺术迷宫里。而宫殿内的怪异静默和宫殿外的日常喧嚣,一个“特等梦”带来的至亲的人头落地和马克-阿莱姆的迅速擢升,小说里对梦的管控与现实中对思想的审查,也常常在阅读中被置放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有的令人恐怖的黑色幽默。
从《亡军的将领》开始,卡达莱就显现出书写民族心灵史的动机,其中最动人心魄的是《破碎的四月》:
一个小伙子,在雪野中瞄准了他的邻居,枪响人落,他走过去,按照习俗,把死者的枪放到他的脑袋旁,然后告知全村,然后申请了30天休战协定,参加了死者的葬礼,然后尊父命走一天的路程去交血税。这是对半年前一桩血案的复仇,而那桩血案又是对更前一桩血案的复仇……这样的循环血案已经发生了44起,持续了70年,双方家族各堆起了22座坟墓。而这一切都源自70年前一位陌生人的投宿。清晨,陌生人离开了,却在村边被邻居开枪射杀,按照卡奴法典,陪伴过客人的人就要负起复仇的责任……
小说中分别写了几组人物,但焦点却是一部扎根于北部高原人心中的卡奴法典。无论是背负血债的复仇者乔戈,还是在高原上蜜月旅行的作家夫妇,抑或是阴郁城堡内的嗜血的官家,皆成为体现或观察卡奴法典的流动的视角。结果,法典比作家成功塑造的几组人物更加栩栩如生:它的崇高性,它之于高原人的那种血性、生命感和一诺千金的规范性,还有它的血腥和破坏性,以及隐藏其中的某种奇妙的平衡……它是那么有魔力,以致让热情赞美者走向某种悖反,让怀疑者不由自主地亲近它的结果。小说中的多重流动视角,不仅具有叙事功能,也是思想性的,与现实中的思维一律构成强烈反差;或者反过来说,即使阿国再思维一律,也容得下一种对话性的小说思维。
是不是例外?
还有一个问题萦绕心头:卡达莱是否只是阿尔巴尼亚文学的一个例外?
由于没有更多中译本,很难直观地得出结论。但据翻译家郑恩波先生透露,卡达莱不是孤立的,他只是阿国文学众多璀璨明星中耀眼的一颗,“摆在同一个天平上的杰出人物”,还有阿果里、马尔科、佐泽、斯巴秀等,只是我们很少能读到他们的作品。中译本似乎只有阿果里的《居辽同志兴衰记》(重庆出版社,2009)和《阿果里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就改编于阿果里小说《迈默政委》。
我读卡达莱时,又重看了这部老电影,其中有一个片段令我惊讶不已:外面,德国人正搜捕进城做手术的易卜拉欣;家里,易卜拉欣却指责冒死收治他的医生也给德国伤兵治病,医生回答:“我了解你,有某种信念的人,为了坚持信念总是把问题简单化……”易卜拉欣认为医生给游击队员看病只是“受朋友之托”,没什么了不起,但“为了害怕德国人而去工作,那还是得承担责任。”(含有未来审判意味)医生回答:“你是按照你的标尺来衡量人的。”在“中立即罪”、“不纯即罪”的意识形态主宰性声音之外,还能“复调”出“你是片面的、有限的”声音。
这让人更加好奇,想知道卡达莱及他的同胞在社会骤变后,又是如何反思那段历史的。可惜,在目前出版的六部中译本中,只有《错宴》属于这个范畴。但我们仍然可以一斑窥豹,见识到作者反思历史的宏大视野:
吉诺卡斯特城有两位著名医生:留学德国的大古拉美托和留学意大利的小古拉美托。他们仿佛不是生活在自己的寓所或医院里,而是生活在城里各种对立的闲谈和舆论里。意大利人占领了城市,小古便被推入舆论的中心,有褒有贬;与此同时,大古作为映衬,也被带入风暴的中心,有贬有褒。意大利人走了,德国人来了,他俩的位置又掉了个个儿,同样被推进舆论的风暴……但这回却是德军上校点名要见大古,据说大古去了,也邀请了上校赴他的家宴,但谁也没有看到。人们看到的只是大古家的灯光亮了一夜,还传出了悠扬的音乐。“叛徒!”有人骂道。“不,英雄!”有人赞道。但那一晚,被德国人抓去的80个人质,包括一位犹太人,全部释放了。
解放后,大、小古拉美托在经历了短暂的错捕后,一直平静地服务他们所在的医院。但到了1953年,一桩离奇间谍案又把大古裹挟其中。起因是他当年救下的犹太人从以色列寄来的一封信,但却正值克里姆林宫“间谍案”发生,一个来自领袖的小小怀疑,被发展为具有国际背景的犹太人阴谋,牵扯到苏联和东欧诸国。东柏林来人了,莫斯科也来人了,大古被拖入神秘的夏妮莎洞穴接受酷刑。
事情远没有仅仅一封问候信那么简单,档案显示,当年医生接待的德国上校也是假的,真人早已战死于苏联。问题不在于医生和德国人勾结,而在于那个德国上校与企图扼杀共产主义的犹太人组织勾结。终于,斯大林死了,莫斯科的人也回去了,但因痛失国际领袖而精神崩溃的本国办案者,却私自处决了这个已为城市做过12000次手术的著名医生……
翻译家高兴说,“提起阿尔巴尼亚,许多人往往会随口说出两个人的名字:恩维尔·霍查和伊斯梅尔·卡达莱。”的确,仿佛有缘似的,在一盏明灯从欧洲陨落后,又一盏明灯在悄然升起……
本文作者:南方周末
-
Tags: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