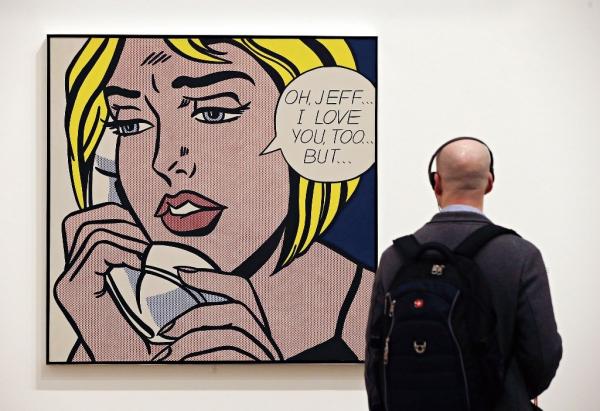典故里的中国:负罪的圣王历史文化

毛泽东与黄炎培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来到了延安,与毛泽东在窑洞里长谈。黄炎培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周期律”: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直到国民党时代,都难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规律,兴起时如此蓬勃,而灭亡时又如此迅速。而毛泽东也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出路,那就是让人民监督我们。”
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语,最早出自《左传 庄公十一年》,原话是“禹汤之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之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像大禹、商汤这样的圣王,因为能自我批评,自我归罪,所以他们的兴起才这么蓬勃,而古代暴君夏桀、商纣,因为总是把罪责推给别人,所以亡国只在一瞬间。圣王罪己的记录,最早见于《论语》的《尧曰》篇:上古君王舜在告诫自己的继承人禹的时候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意思是“如果我犯了错误犯了罪,那么我又有什么资格统治天下呢?而假如天下某个地方有人犯了罪,那么说到底仍然是我犯的罪。”孔子把这段话反复念诵,其意图不难明白。这句话在《尚书 汤诰》中变成了商汤说的,当然《汤诰》篇可能是晋朝人梅赜伪造的,可信度自然远不如《论语》。后来这段话在《后汉书·陈蕃传》里又多了一个情景:大禹在苍梧视察时,遇到有人杀人,于是下车哭道:“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这句话在这里,便从原来假设的口吻变成了实实在在发生了的情况,而大禹王毫不犹豫便把罪责担了下来。

大禹治水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缺乏“罪感文化”,比如旅美学者刘再复先生在《罪与文学》中就认为中国文化中因为缺少了基督教的“原罪”思想,所以缺乏忏悔精神。刘先生忽略了经书中舜、禹、汤这一类自钉十字架的圣王,进而得出中国缺乏罪感文化和忏悔精神,这十分遗憾。罪感源于宗教感却又不限于宗教感,任何一个勇于自省的人都自然而然地会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进而产生某种欠负感。宗教与道德常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体两面。当然,我们也不能将禹汤的罪感与基督教的罪感相等同。基督教的罪感乃是民众共有的,有了罪感才有赎罪进而得救的可能,但禹汤的罪感却更多地是作为政治家和君王的责任伦理,是对天下国家高度负责的自然结果。德国学者马克斯 韦伯认为儒家伦理是一种“信念伦理”而不是“责任伦理”,只看动机,不看效果,只求发善心,不求担责任。但禹汤这种人饥由己饥之的担当,仅仅靠信念恐怕不太可能。如果没有对至善虔诚的信念,禹汤也不可能对世间的罪和自己的罪如此敏感,而如果没有基于天下国家的责任担当,禹汤也不可能站出来把罪恶担荷在自己肩上。
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的隔阂与偏见,使我们将传统文化当成了专制的根源,在这种逻辑下,专制的制度产生盲目的权力。却不知传统文化内部也有着一种自我纠偏的机制。权力不是不会犯错误,但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圣王罪己是经书里的启示,也是历代君主的历史经验。下过罪己诏的皇帝就有汉武帝、唐德宗、崇祯帝等。我们不必怀疑历代君主的真诚,不必把罪己当成政治家的作秀(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就从汉武帝“巫蛊事件”后的杀子之痛入手,剖析汉武帝罪己诏的政治原因和心理原因,读来十分感人,让人不得不相信汉武帝的真诚),相反,罪己本身就是内心强大的表现。知耻而后勇,观过而知仁。大哲学家尼采赞美“具有耶稣灵魂的凯撒”,而耶稣背起了十字架。
经典链接
: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论语·尧曰》
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既而闻之曰,公子御说之辞也,臧孙达曰:“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
——《左传·庄公十一年》
本文作者:新浪历史
-
Tags:历史文化